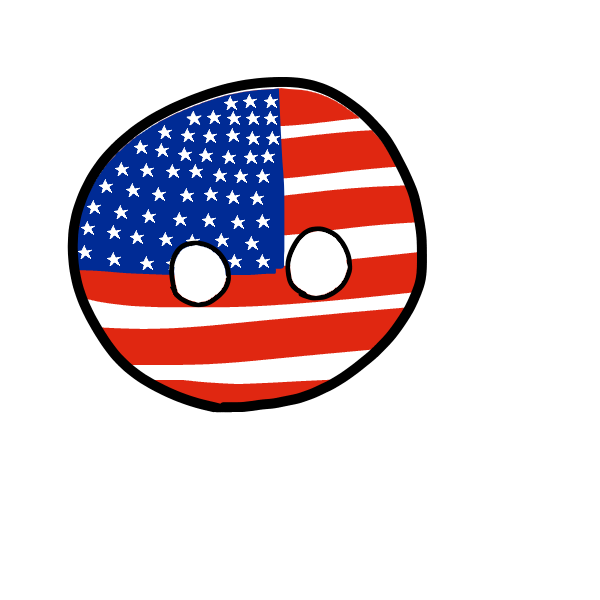就是呃美英对美英
“马德里有37个孩子淹死在了流光中”不列颠淡淡的说了一句。
“光是杀不死小孩子的”美利坚嘟囔了一声,并不在意。
1772年,十三州收到日不落送他的圣诞节礼物,一艘木雕的帆船。那已经是220年前的事了。
哥伦比亚的作家在欧洲写下异乡魔幻的故事,不列颠却想到一件往事。光是可以杀死小孩子的,不列颠想,光曾经杀死了一个小孩子。
那时候还没有电灯吧,不重要,杰斐逊先生手里的油灯一样光亮,一样可以溺死一个孩童。
他记得那个孩子是在什么时候死去的,也知道死总在生的对立面永存。
1776年7月4日,十三州溺死在灯光里,剩下的是美利坚 。
而美利坚自己却不知道,美利坚只以为自己走完了长长的,长长的童年。
1772年日不落给十三州许下一个不会被兑现的诺言,日不落说,等你长大了,我要让你做我最好的水手。
可这里是弗尼吉亚西部,一个见不到大海的城市。
十三州那时候看他的眼神有些复杂,200多年之后不列颠回忆着,发现里面或许有喜悦,有怀疑,有畏惧,可是再也没有钦佩,没有希望。
原来几箱茶叶就撕开了裂痕,无法弥合,无法修复。
或许隔阂的种子早就种下去生了根,只是两个人都懒于察觉,或者说,不愿察觉。
于是一直到7月的夜晚,日不落清楚的感知到了十三州的死亡。
他们的脉搏共享同一个频率。
那一晚日不落感到了窒息。他清晰的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听到那声音慢慢的减弱,消失。
那一晚伊卡斯塔湖下着暴雨,源源不断涌入密西西比河的波涛扰乱着亚美利加的脉搏。
从那一刻开始他们不再是一体,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已然分离。
日不落知道一颗属于他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尽管从表面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日不落感受着和他一样的窒息感,海水已经灌进了身体,于是整个人变得腥咸苦涩。氧气的缺失带来失重感,或许该到了走马灯的时候,十三州会想起什么呢?无法言说。
一个属于他的孩子已经死在了苦涩的海水里,除了他没有人知道。一个属于他的孩子带着一个永远不会被实现的诺言死去了,取代他的将是全新的美利坚。
美利坚不知道十三州死去了,美利坚只以为自己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伊卡斯塔湖的暴雨已经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脉搏,一个独属于美利坚的脉搏。在7月4日谁都不曾发觉的时刻,美利坚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独立的意识体。
现在在密西西比河河畔将再也无法听到泰晤士河游轮上的笑声了,血脉相连已经成为了历史。
已经有200多年过去了,不列颠想着。
200年里沧海桑田,不列颠透过落地窗,看着窗外灯火璀璨。
“216年前,有一个小孩子死去了,而你不知道这码事。”不列颠说,看着窗外的灯火,感觉像一片五彩的海洋。
“那一年死去的小孩子很多。”美利坚说,一双碧蓝的眼睛深处也是和窗外一样汪洋的海。
“流光似水。”他说着,想着。
216年前在一个伊卡斯塔湖暴雨的夜晚里,一个孩子死在了一片没有海的土地。
现在文字中间,37个孩子死在了一幢公寓楼里,在一个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土地上,死于溺水。
魔幻的像他们的过去。
“我不喜欢文学,也不懂隐喻”美利坚说。
隐喻已经使他感到了厌烦,感到了不可言说。他只想要有一天,不列颠卸掉所有伪装,赤诚的站在自己面前。
而不是和这些隐喻打着纠缠不清的交道。
美利坚知道有什么秘密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他却不想知道,也不能知道。
不可说,不能说。
他只能牢牢的扣住不列颠的双手,在窗外五彩的灯影中给他一个吻。
隐喻对他们来说都是可怕的。
不列颠扭头看着窗外的灯光,一片汪洋的海。
感到一种窒息。
他已经不是深谙水性的日不落,他已经失去了船舵的掌控权 。
隐喻下面是不能说的秘密,也是不必说的变迁。
这里是弗尼吉亚华盛顿。
这里的高楼外面有五彩的斑斓的海。
这海围拢起来,不列颠无法挣脱,无法逃离大海。
流光似水。
或许有一天,我会死于弗尼吉亚夜晚的霓虹。不列颠想。
不列颠伸手抱住了美利坚,回他一个绵长的吻。
光不但可以杀死小孩子。
流光似水。
光或许也会杀死我们。
我们在这片充满了过往与秘密的海里浮沉的太久了。





![表情[aixin]-拟人圈](https://ch.baicsi.cn/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aixin.gif) 谢谢喜欢
谢谢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