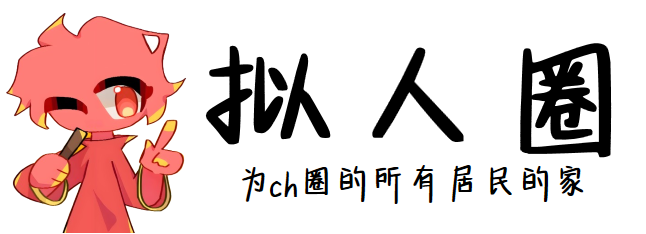莫斯科的雪总比北京来得早。
瓷拢了拢军大衣领口,看着眼前的人——苏正弯腰把最后一根木柴塞进壁炉,羊毛围巾滑到肩头,露出颈间那道被冻伤过的旧疤。火舌舔着木柴发出噼啪声,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块被拉长的红绸。
“你的手还是这么怕冷。”苏忽然开口,转身时手里多了副手套,深棕色的羊皮,指缝里还残留着松节油的味道。这是他前几天用西伯利亚的羊皮鞣的,针脚歪歪扭扭,显然是第一次做。
瓷接过手套时指尖碰了碰他的,对方手背上的冻疮还没好透,结着层暗红的痂。他忽然想起五年前在延安,这人也是这样,裹着件磨破袖口的军大衣,从马背上卸下来一捆捆的步枪,睫毛上的霜花掉在他手背上,像细小的冰针。
“今年的冬小麦收成不错。”瓷把手套戴好,暖意在掌心漫开,“比去年多收了两成,够熬到开春。”
“我让那边再送些拖拉机过来。”苏往壁炉里添了块桦木,火星溅起来,映亮他灰紫色的眼睛,“还有育种专家,他们说你们的土壤适合种冬黑麦。”
墙上的挂历停在1953年的12月,边角被烟火熏得发卷。瓷盯着那页上用红笔圈住的日期——那是他第一次来莫斯科的日子,苏在火车站举着块硬纸板,上面用生硬的汉字写着“欢迎”,北风把他的围巾吹得像面小旗。
“还记得我教你说‘同志’的时候吗?”瓷忽然笑了,“你把‘tong zhi’念成‘dong zi’,被瞪了一眼,脸涨得比甜菜汤还红。”
苏的耳尖泛起红意,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动作和当年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一样。那时瓷刚结束谈判,累得靠在墙上打盹,醒来就看见这人正笨拙地给他盖自己的军大衣,领口沾着面包屑。
壁炉里的火渐渐弱下去,窗外的雪敲打着玻璃,像谁在轻轻叩门。苏从柜子里翻出瓶伏特加,瓶身上的标签已经泛黄。他倒了两杯,推给瓷一杯:“尝尝,今年新酿的,比去年的烈。”
酒液入喉时像团火,瓷咳了两声,看见苏正盯着他笑,眼角的细纹里盛着暖意。他忽然想起这人总说,西伯利亚的白桦林到了春天会开满铃兰,“等你那边安定了,我带你去看。”
“明年……”瓷想说些什么,却被窗外的风声打断。远处传来卡车驶过雪地的声音,大概是送援助物资的车队到了。他知道苏最近为了凑齐那些机床,把自己的军工配额都削减了一半。
苏忽然握住他的手腕,掌心的温度透过手套传过来。“别担心。”他说,声音比伏特加还沉,“我们是同志,不是吗?”
挂历上的红圈被火烤得微微发皱,像片被揉过的枫叶。瓷看着壁炉里渐渐熄灭的炭火,忽然觉得,有些东西比火焰更耐烧——比如那句被风雪吹过无数次的“同志”,比如两个在红旗下并肩站过的影子,哪怕有一天雪会盖住脚印,根也总在同一个地方。
夜深得像口井时,瓷被冻醒了。身边的位置是空的,窗台上多了支刚折的白桦枝,枝桠上的雪还没化,在月光里闪着细碎的光。他披上苏的军大衣走到门口,看见那人正站在雪地里,给援助物资车的轮胎裹防滑链,围巾在风里飘得笔直,像面永不褪色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