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
长久之寂 ,天作之合。 —— 题记
唐宁街的橡木门被风撞得哐当作响,英烦躁地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摔在雕花桌上,羊皮纸锋利的边角在掌心压出红痕。手机在狼藉的文件堆里震动,屏幕亮起法发来的消息,字里行间带着巴黎特有的漫不经心:“泰晤士河又要开茶会了?记得给鲤鱼们发请柬,就用你那顶生锈的王冠当茶托。”
他扯松温莎结,按下通话键:“至少我的泰晤士河不会像塞纳河那样,时不时吞掉几座桥。倒是某人的铁塔,上个月被抗议者挂了满当当的横幅,远看像顶滑稽的毛线帽。”
听筒里传来油画刮刀刮擦亚麻布的刺啦声,混着压抑的轻笑:“哦?上次安理会投票,是谁领带死死缠在我袖扣上,活像中世纪决斗前紧张到打结的骑士?我可记得某人当时耳尖都红透了。”
“那是你香水喷得太浓,熏得人头晕!”英立刻反驳,耳尖却不受控地发烫。
蒙马特高地的晨雾漫进画室时,法正对着未完成的双联画皱眉。左边是滑铁卢的硝烟,右边是诺曼底的海滩,中间本该画鸢尾与蔷薇缠绕的断剑,此刻却空白一片。手机亮起新邮件,1944年的朱诺海滩在屏幕上泛着黄晕——照片里,两个年轻身影立在登陆艇前,他的钢盔歪向左侧,英的风衣被海风掀起猎猎一角。
他叼着烟,指尖在键盘上敲击:“你当年说抢滩要像亲吻玛莱区的姑娘,结果自己摔进海水里,像条翻肚的鳕鱼。我还记得你呛水后咳个不停,却还嘴硬说那是给我示范正确姿势。”
消息刚发出去,就看到对方正在输入。片刻后,消息框弹出撤回提示,紧接着新消息发来:“胡说!要不是为了把你这个冒失鬼拽回来,我会摔?”后面还跟着个被删掉又重新补上的句号,莫名透着股欲盖弥彰的窘迫。
纽约联合国大厦的深夜,英在旋转门前截住抱着文件的法。“中东提案的修正案…”他话未说完,就被带着鸢尾与威士忌气息的靠近打断。
“1904年丽兹酒店,你往白兰地里兑苏打水时,也是这副欲言又止的表情。”法的声音低沉,温热的呼吸扫过耳畔,“当时你紧张得把方糖掉进酒杯,溅出来的酒水还弄脏了我新定制的衬衫。”
“那次明明是你把我的领带当画布,用口红画满鸢尾花!”英后退半步,却撞上消防栓,“还偷走了我母亲给的袖扣,害得我找了整整三天。”
法的拇指轻轻擦过他西装口袋露出的玫瑰花瓣,语气带着笑意:“可你第二天不还是把袖扣别了回来?别告诉我,这也是出于外交礼仪?”
远处安理会会议厅的铜钟突然敲响,惊起玻璃穹顶白鸽扑棱棱的翅膀,洁白的羽毛在灯光下纷纷扬扬,宛如一场无声的雪。
莫斯科零下三十度的战壕里,法费力地掰开冻得梆硬的黑面包:“还记得斯大林格勒的地窖吗?你喝光最后一滴伏特加,红着眼睛说——”
“没有永恒的敌人。”英呵出的白雾在钢盔上凝成霜花,突然扣住对方冻得发紫的手,指腹轻轻摩挲着虎口处那道百年战争留下的剑伤,“只有冻僵的蠢货——比如某个非要把伏特加藏在胸口,结果酒瓶和心脏一起结冰的家伙。”
法笑出声,呼出的白雾与英的缠绕在一起:“那还不是怕某人偷偷独吞?毕竟某人喝多了,可是会抱着我的手臂不撒手,嘴里嘟囔着‘不准离开’。”
呼啸的暴风雪中,两人交叠的影子被投射在结满冰棱的岩壁上,像幅褪色的中世纪双联画,见证着跨越百年的羁绊。
秋分那日,巴黎圣母院的钟声里,英推开古董店的铜铃门。法正在擦拭1815年的怀表,表盖内侧鸢尾与蔷薇的浮雕泛着温润光泽。
“修复师说这是停战代表的信物。”他头也不抬,镊子夹起齿轮时闪过冷光,“和你保险柜里那半枚徽章,倒是意外般配。”
“天生一对。”英的手指轻轻覆盖在怀表表面,感受着齿轮转动的细微震颤,“就像我们。”
塞纳河游船的汽笛撕开薄雾,惊飞梧桐树上的鸽子。阳光穿过彩窗,在他们交叠的影子上洒下细碎的光斑,宛如一幅永不褪色的油画。
一会儿发配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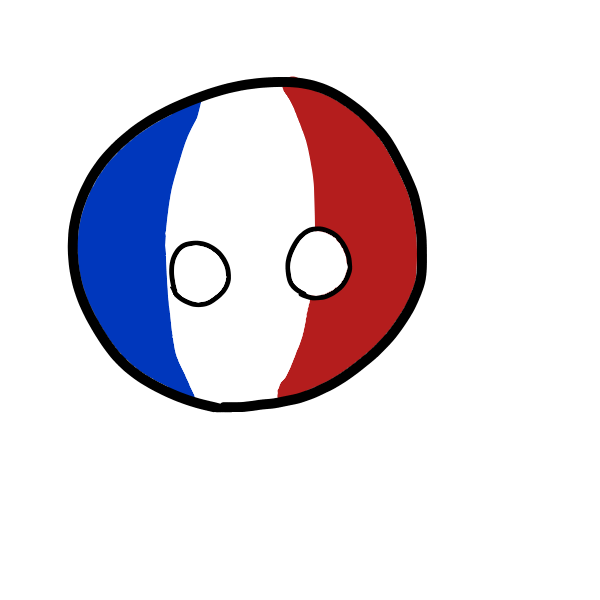


没有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