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专场。
23年4月5日写
1775年的莱克星顿,少年在晨雾中踉跄起身。粗布衬衫下,胸口新烙的自由之火图腾还渗着血珠,他握紧那把刻着“1776”的燧发枪,枪管残留着昨夜与英军交火的硝烟。沾着露水的草地上,散落着康科德村民递来的面包,此刻却在枪声里滚入泥泞。
特拉华河的冰棱割裂他的脚掌,寒风卷着雪粒扑在脸上。对岸的英军营帐灯火通明,而他和饥寒交迫的士兵们,正用冻僵的手推着炮车,冰面下传来隐约的呜咽,像极了母亲临终前的咳嗽。
约克镇的硝烟中,少年嘶吼着冲锋。威廉大叔的铜号声穿透枪林弹雨,却在他眼前戛然而止——铅弹洞穿号管的瞬间,温热的血溅在他脸上。他跌坐在焦土上,颤抖着捡起那支扭曲的铜号,号管内侧的指纹,是无数个训练日夜留下的印记。
巴黎和约签署那日,他站在塞纳河畔。西装革履的外交官们举杯相庆,而他抚摸着胸前褪色的布条星星,忽然想起福吉谷的寒冬。那时他发着高烧,却固执地将星条旗盖在濒死的战友身上,布料吸收的血渍,早已洗不褪色。
当摩天大楼刺破云端,西装革履的男人在联合国会议上侃侃而谈。深夜回到办公室,他总会打开保险箱,取出那支布满弹孔的铜号。月光透过落地窗洒落,照见他后颈未愈的旧伤——那是独立战争时留下的刀疤,至今仍会在阴雨天隐隐作痛。玻璃柜里,褪色的星条旗静静舒展,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再也回不去的、少年在血泊中升起旗帜的清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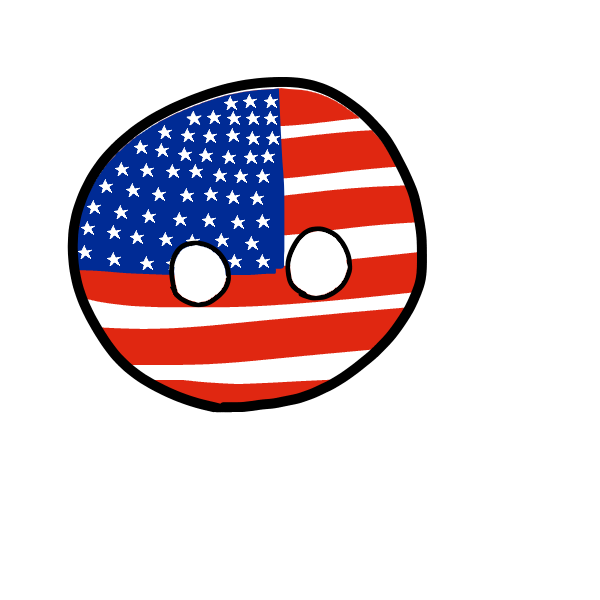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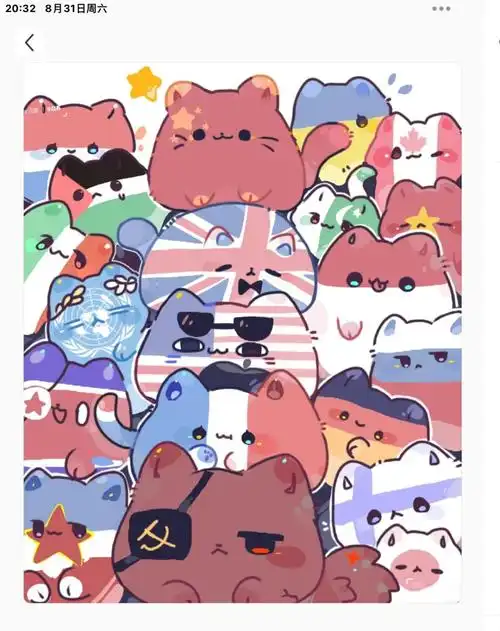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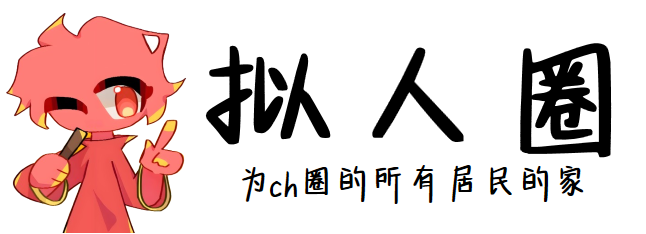
没有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