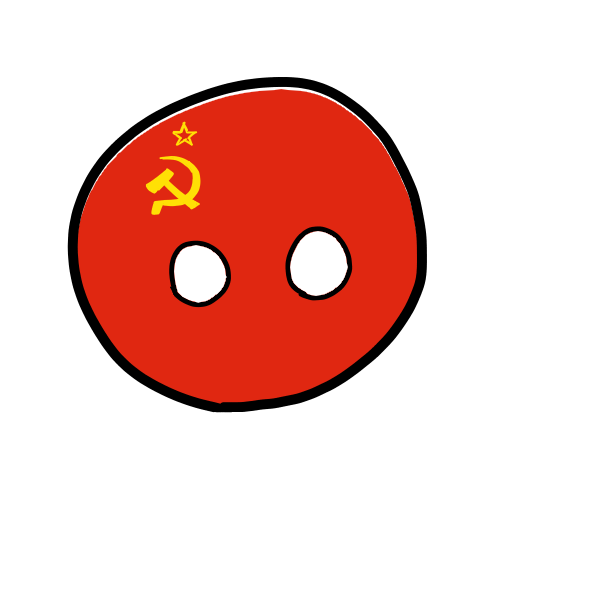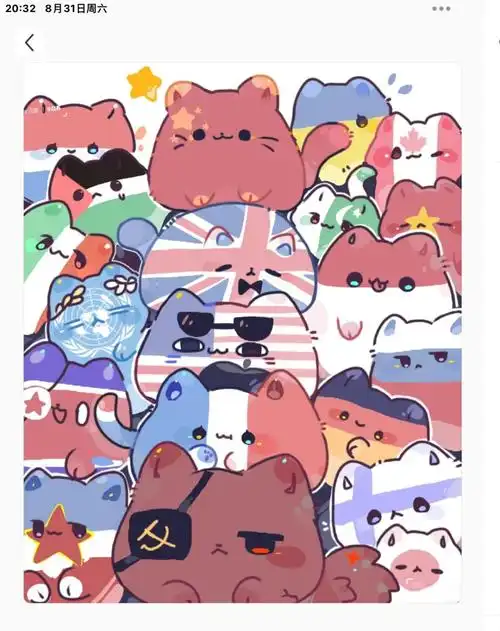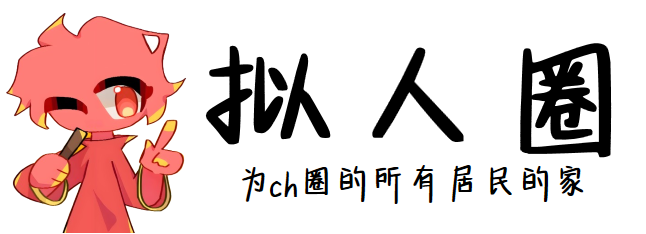苏瓷,历史向。
1945年初春,长白山的暴风雪将世界切割成混沌的白色。瓷蜷缩在废弃矿洞深处,听着伤员压抑的咳嗽声混着呼啸的北风。医药箱早已见底,绷带被鲜血浸透又冻成硬块,步枪里剩下的子弹在掌心硌出红痕。洞外突然传来侦察兵急促的脚步声:“日军的巡逻队带着军犬,最多两小时就到!”
寒气顺着矿洞裂缝渗入骨髓,瓷握紧腰间的驳壳枪,枪柄上“必胜”二字的刻痕早已被摩挲得发亮。那是三年前苏用匕首刻下的,当时他们在松花江畔伏击关东军,苏一边装填莫辛纳甘步枪,一边笑着说:“等胜利了,要带你去莫斯科看真正的雪。”
深夜的风雪突然变得更加狂暴,正当战士们准备背水一战时,矿洞外传来引擎撕裂风雪的轰鸣。瓷扒开被积雪压住的帆布帘,只见一辆涂着迷彩的军用雪橇冲破雪幕,车头绑着的红星在闪电中忽明忽暗。雪橇急刹在洞口,溅起的雪粒打在脸上生疼,苏掀开厚重的防寒罩,睫毛上的冰晶簌簌掉落:“莫斯科的特快专递,签收一下?”
车斗里堆满了冒着寒气的木箱,崭新的莫辛纳甘步枪在月光下泛着冷光,医用保温箱上的俄文“紧急物资”还带着油墨香。苏跳下车时,军靴踩碎冰层发出清脆声响,他扯开大衣,从贴身口袋掏出个铁皮盒:“列宁格勒的医生说,这种磺胺粉对付感染最管用。”瓷注意到他耳后结着的冻疮,还有军大衣下摆新添的弹孔——那是穿越西伯利亚雪原时留下的印记。
“听着,我的朋友。”苏按住瓷的肩膀,蓝色眼睛里燃烧着火焰,“你们从西侧密林突围,我在山口架机枪掩护。记住,莫斯科的火炮能轰开柏林的城墙,小小的关东军更不在话下!”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时,苏已经架起DP轻机枪守在山口,他的军大衣在狂风中猎猎作响,像一面永不倒下的旗帜。
激烈的枪声震落枝头的积雪,瓷带着伤员们在林间奔逃,每跑几步就回头张望。只见苏的身影在硝烟与风雪中时隐时现,机枪喷出的火舌照亮漫天飞雪。当最后一声枪响消散在山谷,瓷带领战士们返回山口,却只看到满地弹壳和日军的尸体,苏和雪橇车都没了踪影。
死寂的雪地里,瓷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就在这时,远处雪坡传来熟悉的引擎声,苏驾驶着伤痕累累的雪橇冲出白雾,车斗里还捆着缴获的日军物资,脸上沾满硝烟却笑得灿烂:“怎么,以为我去见列宁了?”他跳下车时踉跄了一下,裤腿渗出的血迹在雪地上晕开暗红的花。
“受伤了?”瓷冲上去扶住他。苏满不在乎地扯开裤管,子弹擦伤的伤口还在渗血:“在基辅保卫战时,我受过比这更重十倍的伤。”他突然从怀里掏出半块黑面包,硬得能砸开核桃:“尝尝,还是莫斯科的味道。等战争结束,我们要在红场喝伏特加,看坦克从列宁墓前驶过!”
多年后,瓷站在中苏边境的纪念馆里,玻璃展柜中陈列着那把刻着“必胜”的驳壳枪,旁边是泛黄的俄文信件。窗外的长白山依旧白雪皑皑,当年的弹壳早已锈迹斑斑,可那段在血与火中淬炼的情谊,却如同山顶终年不化的冰川,在岁月长河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超越了国界与语言,见证着两个民族用热血与生命,共同铸就的、永不熄灭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