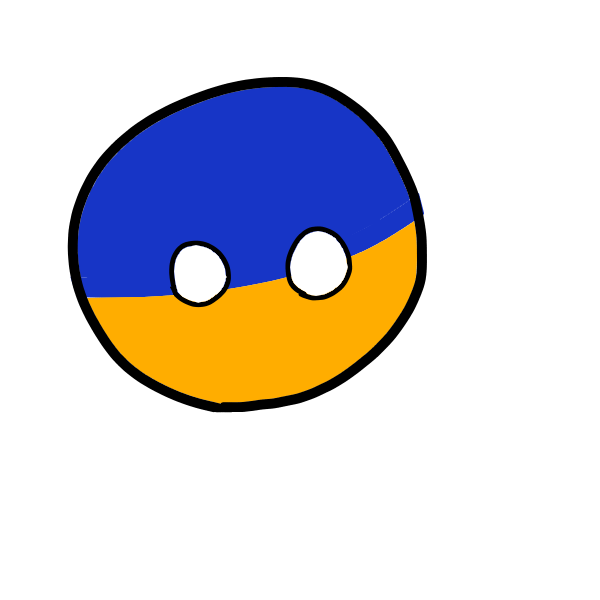乌克兰站在第聂伯河畔,风吹过他浅金色的头发,那双眼睛——那片比天空更浅的蓝色里,沉淀着土地所有的丰饶与苦难,眉宇间总锁着一层化不开的愁。
克里米亚的风从南方吹来,带着咸涩的海盐味,却吹不散他眼底的雾。
1945年,基辅的春天来得特别迟。乌克兰跟在高大的苏维埃身后,参加胜利日的阅兵。他的军装有些宽大,袖口需要折两折才能露出手腕。胸前的勋章是苏维埃亲手别上的,为了表彰他在战争中的“贡献”——尽管那些贡献往往意味着失去。
“站直。”苏维埃低声说,手放在乌克兰肩膀上,力道不轻不重。
乌克兰挺直了脊背,但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对面。在盟军的队伍里,美利坚正笑着和英吉利说话,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似乎是感受到了注视,美利坚转过头来,朝他笑了笑。
乌克兰迅速低下头,耳朵微微发红。
“不要东张西望。”苏维埃的声音更低了,带着警告。
阅兵结束后,乌克兰独自走到被炸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战争结束了,但基辅一半成了废墟。他的手抚过斑驳的墙壁,指尖沾上了历史的尘埃。
“很美的建筑,可惜了。”
乌克兰猛地转身。美利坚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笑得随意又好看。
“美利坚先生。”乌克兰恭敬地点头。
“叫我美利坚就好。”他走近,仔细打量着乌克兰,“你就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比我想象的年轻。”
乌克兰抿了抿唇没说话,他不太喜欢被说年轻。
美利坚笑了,顿了顿,“战争期间,你们受苦了。”
乌克兰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是的,他们受苦了——先是纳粹的占领,然后是苏联红军的“解放”,再然后是饥荒。他的子民们在短短几年间死去了数百万,而他只能看着,无能为力。
“苏维埃对你怎么样?”美利坚突然问。
乌克兰警惕地抬头:“苏维埃同志是我们的领袖,是兄弟民族的保护者。”
“兄弟?”美利坚挑眉,然后轻轻摇头,“你知道吗?真正的兄弟不会让弟弟挨饿。”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进了乌克兰心里最柔软的地方。1932-1933年的大饥荒,饿殍遍野,人相食。他跪在克里姆林宫门前恳求,得到的只是苏维埃冷静的回应:“必要的牺牲。”
“我得走了。”乌克兰低声说,转身想要离开。
“等等。”美利坚拉住他的手腕,然后迅速松开,“如果有需要……可以来找我。”
乌克兰没有回头,只是快步走开。但他的心跳得很快,快得让他害怕。
1954年,克里米亚。为了庆祝“兄弟情谊三百年”,苏维埃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名下划给了乌克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庆典上,乌克兰接过了文件,脸上努力挤出笑容。
克里米亚站在他身边,这个黑海边的少年有着鞑靼人的深邃眼睛和俄罗斯人的骄傲。他不太情愿地伸出手,乌克兰握住了,感觉到对方掌心的抗拒。
“好好照顾他。”俄罗斯在一旁说,语气平静,但眼神复杂。
乌克兰点头,转向克里米亚:“欢迎回家。”
克里米亚勉强笑了笑,没说话。
晚上,乌克兰独自坐在黑海边。克里米亚走过来,坐在他身边。
“你知道这不是礼物,对吧?”克里米亚突然说。
乌克兰转头看他。
“这是一个负担。”克里米亚捡起一块鹅卵石,扔进海里,“一个烫手的山芋。海军基地,战略要地,现在成了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弱点。”
“我知道。”乌克兰轻声说。
他们都沉默了,只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
“你眼睛里的愁,是从哪里来的?”克里米亚突然问。
乌克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个苦涩的笑:“从我的土地里和每一个死去的灵魂里。”
1975年,赫尔辛基。欧安会议上,乌克兰作为苏联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他已经不再穿宽大的军装,而是合身的西装,但眉间的愁却更深了。
美利坚找到他时,他正在阳台上抽烟。
“你学会抽烟了。”美利坚靠在栏杆上。
乌克兰没有看他:“很多年了。”
“你看起来……”美利坚斟酌着用词,“很累。”
乌克兰终于转头看他。三十年了,美利坚几乎没变,还是那样耀眼,那样自信。而他自己,感觉已经老了很多年。
“切尔诺贝利。”乌克兰只说了一个词。
美利坚的表情严肃起来:“我知道。我很抱歉。”
“你的中情局早就知道那地方有问题,不是吗?”乌克兰的语气带着罕见的尖锐,“但你们什么也没说,因为那是苏联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
美利坚无法反驳。他确实知道,确实什么也没说。
乌克兰把烟按灭:“有时候我觉得,你们俩——你和苏维埃——没有本质区别。都把世界当成棋盘,把我们当成棋子。”
“不是这样的。”美利坚说,但声音缺乏底气。
“那是怎样的?”乌克兰直视他,“告诉我,美利坚先生。当你们在日内瓦谈论限制核武器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核战争爆发,第一个被抹去的就是基辅、明斯克、华沙?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兄弟国家’,其实是你们对抗的最前线?”
美利坚沉默了。风吹过,带来波罗的海咸湿的气息。
两个人沉默着,“抱歉。”美利坚最后说。
乌克兰摇摇头,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他停下来,没有回头:“那年你说,如果有需要可以找你。现在我需要了,你能给我什么?”
美利坚想说“自由”,想说“援助”,想说“保护”。但最终,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乌克兰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他什么也给不了。至少现在还不能。
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乌克兰站在基辅独立广场上,看着人群聚集。他们挥舞着蓝黄旗帜,高呼“自由”。他的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陌生的希望。
克里米亚站在他身边:“你真的要这么做?”
“我必须。”乌克兰说。
“苏维埃不会允许的。”
“苏维埃快死了。”乌克兰轻声说,语气里没有喜悦,只有深深的悲哀。
他爱过苏维埃,像孩子爱父亲,像弟弟爱兄长。但爱不能抵消伤害,不能弥补失去,不能治愈伤痕。
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投,90%的人支持独立。当结果公布时,乌克兰哭了,七百多年来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流泪。
12月25日,苏维埃消失。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联合国席位,而乌克兰,终于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1994年,乌克兰交出了苏联留下的核武器——世界第三大的核武库。作为交换,美国、英国和俄罗斯承诺保障他的领土完整和安全。
美利坚在文件上签字时,抬头看了乌克兰一眼。他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那一刻,美利坚想起了1945年的那个少年,眼睛里有化不开的愁,但至少还有一丝光。
现在,光几乎熄灭了。
“你会信守承诺吗?”乌克兰轻声问。
“我会。”美利坚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
但乌克兰只是笑了笑,那笑容里的悲哀深不见底。
2014年,克里米亚。乌克兰站在基辅的办公室里,看着电视屏幕。俄罗斯军队接管了克里米亚,那个黑海边的少年——不,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宣布要“回家”。
克里米亚打来电话:“对不起。”
乌克兰没有说话。
“他们说会举行公投,但我已经知道结果了。”克里米亚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只是……我只是想要更强大的保护。”
“我明白。”乌克兰说,声音平静得可怕。
挂断电话后,他走到窗前。基辅的春天又来了,第聂伯河开始解冻。但这一次,他感觉不到温暖,只有刺骨的寒冷。
美利坚打来电话,谴责俄罗斯的行为,宣布制裁,承诺支持乌克兰。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充满了正义感。
“你会出兵吗?”乌克兰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
“不会,对吗?”乌克兰笑了,“因为那意味着与俄罗斯直接冲突,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我理解,美利坚先生。我理解。”
“乌克兰,我……”
“不用说了。”乌克兰轻声说,“我习惯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棋子,不是棋手;一直是土地,不是国家;一直是牺牲品,不是主角。”
他挂断了电话。
现在,乌克兰依然站在第聂伯河畔,眉间的愁更深了,深得像是刻进了骨子里。
东部的战争还在继续,每天都有年轻的生命消失在那片土地上。克里米亚成了遥远的梦,一个他再也回不去的家。而西方承诺的援助,总是来得太迟,太少。
有时候他会想,如果1945年那个春天,他接受了美利坚的邀请,走向了另一边,现在会怎样?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风吹过,带来基辅的钟声。乌克兰闭上眼睛,让那声音包裹自己。
他的土地依然肥沃,他的人民依然坚韧,他的文化依然灿烂。但那双浅蓝色的眼睛里,那片化不开的愁,也许永远都不会消散了。
因为有些伤痕,时间也无法治愈;有些失去,永远无法弥补。
乌克兰睁开眼睛,望向东方,望向那片广袤的土地。那里有他的过去,他的伤痕,他的爱恨纠缠。
他轻声说,声音只有自己能听见:
“我只是想要自由地活着,为什么这么难?”
风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吹着,吹过第聂伯河,吹过基辅的街道,吹过这片多灾多难却又永不屈服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