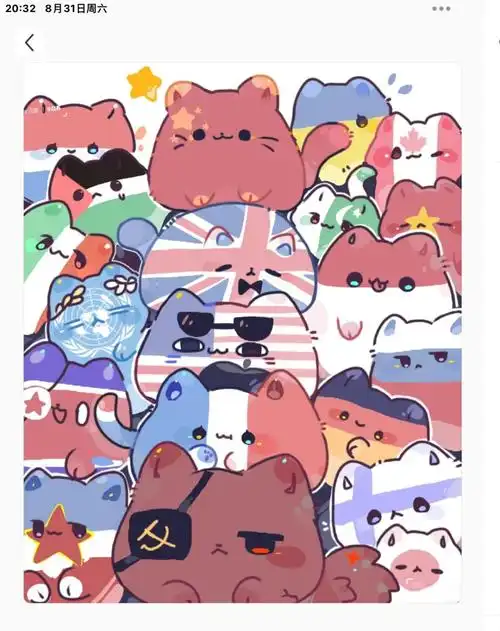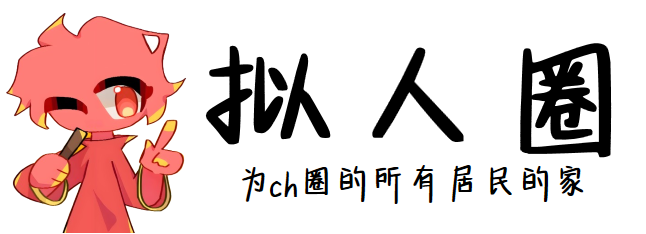雾中的蔷薇
英,单人向
存在的意义在于手握人生终将归于空寂的认知,却始终热烈地生长。 ——文案。
伦敦的雾总在黄昏时漫过泰晤士河,把大本钟的轮廓泡成幅晕染的水彩。英站在威斯敏斯特桥的石栏旁,指尖抚过被雨水浸得发潮的浮雕——那上面刻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船锚,链环的纹路里还卡着1940年的弹痕,像道没愈合的疤。
他兜里揣着半块冷掉的司康,是街角百年面包店买的。纸袋装着的黄油香混着雾的湿,让他想起1897年的钻石庆典,白金汉宫广场上堆成山的糕点,银质餐盘映着全球殖民地的旗帜,风卷着流苏,像片永不落幕的海。可现在广场上的鸽子啄着游客掉落的薯条,他数过,旗杆上的旗帜比当年少了七十六面。
“帝国的太阳总会落的。”老首相当年在唐宁街的壁炉旁说这话时,雪茄灰落在天鹅绒地毯上,像颗早逝的星。英那时正用羽毛笔修改非洲殖民地的地图,笔尖在“埃及”二字上顿了顿,没接话。后来他亲眼看着星条旗取代米字旗插遍大洋,看着总督府的铜匾被拆下来熔成炮弹,看着BBC的新闻里,“大英帝国”四个字渐渐被“联合王国”取代。雾里的风裹着河腥气灌进领口,他忽然笑了,原来所谓空寂,不是轰然倒塌的巨响,是弹痕里长出的青苔,是旗帜褪色后露出的亚麻底色,是终于承认:没有永不沉没的船。
转身走进街角的二手书店时,铜铃在头顶叮当作响。店主正用牛皮纸包一本1923年版的《尤利西斯》,封面上的咖啡渍和英书房里那本如出一辙——当年他在都柏林的酒馆里,和乔伊斯争论文法,威士忌洒在书页上,晕出片琥珀色的云。现在书架最上层摆着本崭新的科幻小说,作者是个巴基斯坦裔女孩,腰封上印着“伦敦出生”,旁边堆着的《莎士比亚全集》里,某页夹着张褪色的戏票,是1953年《哈姆雷特》首演夜的,他记得那天女王的王冠在包厢里闪着光,而他在后排啃着三明治,看“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撞在天鹅绒幕布上,震落了片灰尘。
暮色深了,他往西区的剧院走。《悲惨世界》的海报在雾里泛着光,检票员笑着和他打招呼——这张脸从穿校服的少年变成鬓角染霜的中年人,而英手里的票根,从纸质的泛黄存根,变成了手机里的电子码。幕布升起时,冉阿让的歌声撞在穹顶上,他忽然想起1603年环球剧院的木棚,莎士比亚站在台边,看观众把苹果核扔向哈姆雷特,而现在的舞台上,全息投影的星光落满观众席,有个穿汉服的姑娘正用手机录下“我曾梦见过生活”的合唱,屏幕的光映在她眼里,像当年环球剧院外的火把。
走出剧院时,雾散了些。月光淌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纳尔逊柱上,柱基的浮雕刻着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硝烟,而广场上的年轻人正围着街头艺人跳探戈,踢踏声惊飞了停在狮像头顶的鸽子。英买了支冰淇淋,薄荷味的,甜得发苦,像他在马岛战争结束后,独自坐在福克兰群岛的礁石上吃的那支。那时海浪拍着礁石,像在重复“结束了”,而现在探戈的旋律里,有个巴西男孩正教英国女孩转圈圈,他们的笑声混着冰淇淋融化的甜,滴在石板路上,洇出小小的亮斑。
他沿着河岸往回走,鞋跟敲在石板上的声,和三百年前马车驶过的节奏重合又错开。圣保罗大教堂的尖顶在月光里亮着,二战时被炸毁的穹顶早已修复,只是新石料的白,比旧墙的灰更扎眼。有个穿风衣的老人坐在教堂台阶上拉小提琴,拉的是《绿袖子》,琴弦的颤音里,英仿佛看见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舞会,裙裾扫过地板的声,和现在街头滑板碾过路面的响,在雾里缠成了线。
走到家门口时,钥匙插进锁孔的瞬间,他摸了摸口袋——那半块司康还在,黄油香混着雾的湿,像个温柔的提醒。壁炉上的相框里,有张褪色的黑白照:维多利亚时代的他站在印度的泰姬陵前,西装笔挺,身后是飘扬的米字旗;旁边是张新拍的彩照:他蹲在伦敦眼的阴影里,给个尼日利亚裔小孩系鞋带,背景里的摩天轮正转出彩色的光。
窗外的雾又浓了,把路灯的光泡成团暖黄。英给自己泡了杯红茶,茶包在瓷杯里转着圈,像个缓慢的漩涡。他知道,那些船锚会继续生锈,那些旗帜会彻底褪色,那些“日不落”的旧梦,终将被雾泡成透明。可此刻茶杯里腾起的热气,书架上不断增厚的新书,剧院里永远年轻的台词,还有街角面包店每天清晨出炉的司康香——这些热烈的、琐碎的、明知会被时光磨成尘埃却依然存在的瞬间,或许就是存在的意义:看清了终点的空寂,却依然要在途中,种出满墙的蔷薇。
雾里的钟声响了,十一下。英呷了口茶,舌尖的涩混着甜漫开,像他看过的无数个黄昏:雾会散,太阳会落,但总会有新的清晨,带着面包香,带着书页声,带着不知疲倦的歌声,撞进雾里来。





![表情[zaijian]-拟人圈](https://ch.baicsi.cn/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zaiji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