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联盟的破裂
莫斯科的雪总是下得格外凛冽。1969年的寒冬,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里,暖气开到了最大,却驱不散弥漫的冷意。
瓷坐在长桌的一端,深蓝色的中山装熨帖整齐,袖口露出他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对面是苏,一身军装笔挺,勋章在吊灯下泛着冷光。他们之间,那份曾以鲜血与理想浇筑的盟约,此刻像一张脆弱的纸,被无声的对峙撕出裂痕。
瓷的手指在桌下微微蜷缩,指甲掐进掌心。他想起之前在长波电台的争吵。那时苏曾拍着图纸对他说:“这是为了共同防御,兄弟之间无需计较得失。”
可当瓷提出主权问题时,对方眼底的灰色骤然暗沉,仿佛熔岩在冷却。还有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时留下的半截工程,像一具具未完成的骨架,横亘在哈尔滨的冻土上。那些被撕毁的协议文件,每一道伤口都结痂,却在今夜被再度撕开。
“瓷,你执意要撤回边境驻军?”苏的声音带着金属般的质感,眼底的灰色瞳孔在阴影里忽明忽暗,“这是背叛。”
瓷深吸一口气,喉结滚动。他望向苏身后墙壁上悬挂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副本——泛黄的纸张在暖光下泛着诡异的温柔,仿佛一封早已失效的情书。
他想起1949年,苏在红场上亲手为他披上的那件厚重的军大衣,羊毛里还残留着伏特加与硝烟的味道。
“老师。”他开口,声音平稳如旧,却裹着一层冰,“我们早该明白,没有人能永远为另一个人掌舵。您教会我如何锻造自己的钢铁,如今,我的高炉也该点燃了。”
苏猛地起身,军靴碾过地毯。他逼近瓷,呼吸喷洒在对方发凉的耳畔:“你是我亲手扶起的学徒,用我的钢铁、我的思想浇灌而成。现在你要折断翅膀?”
他的指尖划过瓷的领口,像多年前指导他系第一枚纽扣时的动作,只是如今力道重得能听见布料纤维的呻吟。
瓷的脊背绷直如剑,却未后退。他看向苏肩上新别上的那枚鹰翼徽章,忽然轻笑,那笑声在空旷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锋利:“老师该明白,雏鸟总要自己学会飞翔。您给的羽翼固然温暖,但——”他抬手抚上苏的手腕,掌心推拒着对方的力量,“羽翼之下,永远长不出自己的骨骼。”
窗外的暴风雪骤然加剧,玻璃震颤如战栗。苏的瞳孔骤然收缩,眼底红光近乎暴烈。
他想起1954年,瓷在莫斯科郊外的雪地里,握着冻僵的双手写下第一份工业计划书;想起1956年,他们并肩站在克里姆林宫塔楼,眺望共产主义理想的星辰。可那些记忆此刻都成了刀刃,割裂着他们共同的幻觉。
“若你走出这扇门,我们便是战场上的敌人。”苏的声音沉入地底,勋章在胸前发出刺耳的叮响,像是断裂的誓言。
瓷没有回答。他缓缓起身,中山装的衣摆扫过桌角。袖口残留的薄茧摩挲过桌面——那是数十年书写“同志”二字留下的痕迹。他转身走向大门,靴底碾过地毯上的雪痕。门合上的瞬间,风雪涌入缝隙,将两人的影子割裂成永不相交的两条线。
走廊尽头,瓷的副官递来围巾。他裹住脖颈,却仍觉寒意刺骨。副官低声报告:“边境部队已待命撤离,但苏联在珍宝岛的增兵……”瓷打断他:“按计划执行。”他的目光穿透风雪,望向远方模糊的东方天际,那里有未完成的铁路、有饥饿的田野、有等待觉醒的黎明。
苏独自留在会议室。他抓起瓷遗落的钢笔——那支1949年赠予对方的礼物,笔帽上还刻着“互助”二字。钢笔在掌心旋转,最终被他掷向墙角,墨水溅在泛黄的条约副本上,晕开一片血色。
(闪回:1954年)
莫斯科郊外的雪地里,瓷裹着苏的军大衣,在冻土上踉跄前行。苏举着图纸大笑:“看,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工厂!钢铁将让世界颤抖!”瓷的指尖被寒风割裂,却紧攥铅笔记录数据。那时,他们真的相信,同志的情谊能融化所有冰原。
(闪回:1960年)
哈尔滨的工厂废墟里,瓷蹲在生锈的机床旁,苏联专家撤离时留下的半截工程像一具死去的巨兽。他捡起地上的俄文图纸,用中文在背面写下:“自力更生”。
(闪回:1969年,会议前夜)
瓷在使馆房间彻夜修改撤军文件。他拧开苏赠予的钢笔,墨水瓶底沉淀着过去的二十年。笔尖悬在纸面,迟迟未落,直到东方微亮。
十年后,南斯拉夫的使节在瓷的办公室提及苏联的动向。瓷的茶杯在掌心转了一圈,热气早已散尽。他望向窗外改革开放初期的晨曦,淡笑:“有些裂痕,是必须跨过的深渊。跨过去,便是重生。”墙上悬挂的新地图,边境线蜿蜒如愈合的伤口,而中心位置,一座钢铁城市正在崛起,高炉的火焰映红了天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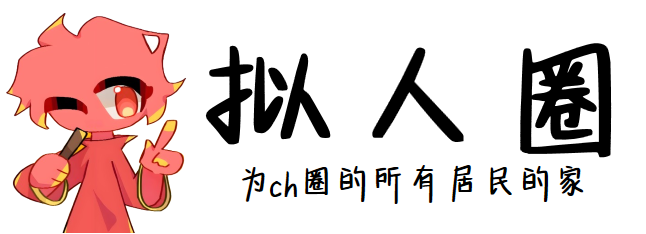
没有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