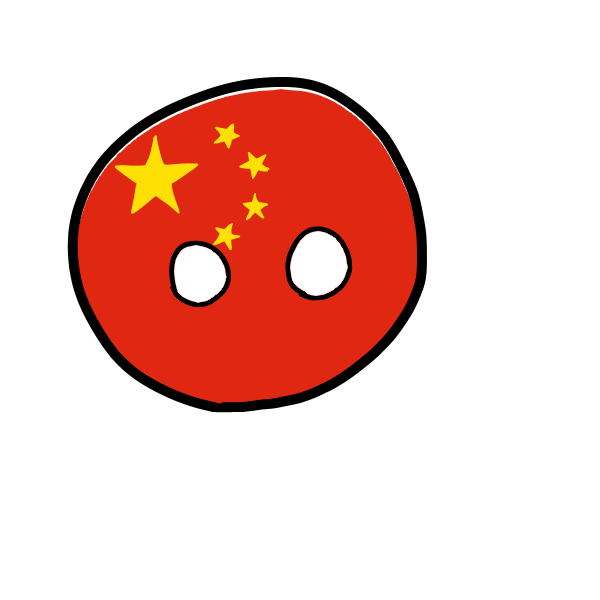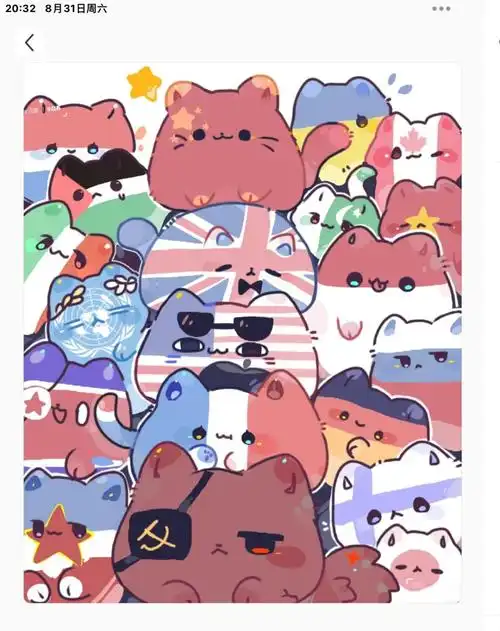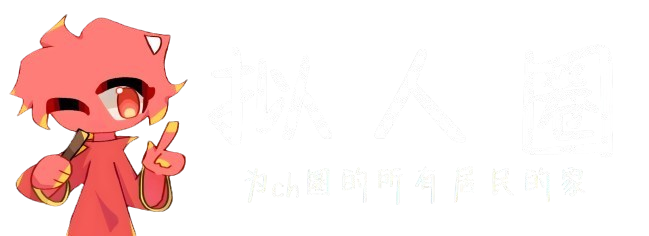单人向,瓷,微历史向。
历史不过是麦子熟了几万次。 ——文案。
瓷蹲在黄河故道的麦地里时,裤脚已经被露水浸得发沉。新麦的芒尖蹭过手背,刺出细密的红痕,像谁用针尖在皮肤上绣了片细碎的星子。他没在意,只是伸手拨开眼前的麦秆,指腹碾过饱满的麦穗,壳子裂开的脆响里,飘出股青气,混着底下黑土的腥甜——这味道,他记了太多年。
脚边扔着把青铜镰,是仿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形制,刃口被磨得薄如蝉翼,映着天上慢慢移动的云。瓷拿起镰,试着割了两垄,动作熟稔得像是昨天刚做过。弯腰时,后腰的旧伤隐隐发疼——那是1960年麦收时留下的,为了抢收被暴雨淋了的麦子,他在泥地里跪了三天,起来时腰像断了似的,老农给他贴的草药膏味,现在想起来还呛鼻子。
日头爬到三竿高,麦芒在光里闪着金,晃得人睁不开眼。瓷坐在捆好的麦秸上歇脚,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搪瓷缸,缸身印的“农业学大寨”字样早就磨没了,只剩个模糊的轮廓,边缘磕出的豁口,是那年在田埂上追跑的孩子撞的。他往缸里倒了些凉白开,水顺着豁口漏下来,滴在麦茬上,洇出小小的湿痕,像滴没忍住的泪。
水喝到一半,他忽然停了。缸底沉着几粒麦壳,是刚才倒水时带进来的,形状歪歪扭扭,像他小时候在生产队晒谷场捡的那些。那时候他总蹲在谷堆旁,把饱满的麦粒挑出来,装进铁皮盒,老农看见了就笑:“瓷娃,这几粒顶啥用?”他不说话,只是把盒子捂得更紧——后来饥荒时,就是这盒子里攒的麦粒,掺着野菜煮成糊糊,救了隔壁病床上的娃。
风从河道里卷过来,带着黄河水的腥气,掀动起无边的麦浪。瓷站起身,看麦浪一波波往天边涌,像极了他见过的无数个夏天:见过秦汉时的农夫光着脚在地里踩,木耒在泥里划出深沟;见过隋唐时的水车转得吱呀响,渠水顺着田埂漫进麦根;见过明清时的灾年,流民跪在干裂的地里,把最后一把麦种往土里塞。现在的麦地里,联合收割机正突突地跑,履带碾过麦茬的声音,盖过了风声,可瓷总觉得,能听见千百年前的喘息,和现在的,重叠在一起。
他沿着田埂慢慢走,鞋底沾满了湿泥,每一步都陷下去半寸。泥里混着麦茬的断口,扎得鞋底发痒,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看。走到地头时,看见块被收割机撞倒的界碑,上面刻着“民国三十七年”,字已经被风雨蚀得浅了,可还能看出笔锋里的急——那年刚打完仗,村民们抢着立碑分地,把“谁种谁收”刻得比啥都深。瓷蹲下来,用手把碑扶直,指尖触到碑缝里的麦壳,是去年的,已经干透了,一捏就碎。
天近黄昏时,他开始往回捡那些被收割机漏下的麦穗。动作很慢,像在数自己的指纹。捡着捡着,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铺在麦茬地里,像条没尽头的路。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变成了这地里的一茬麦:扎根,拔节,抽穗,然后被割倒,打成粮,磨成面,最后又回到土里,等着下一季的风。
布袋渐渐鼓起来,沉甸甸地坠在肩上。瓷摸出颗麦穗,用指甲掐开,饱满的麦粒滚在掌心,泛着珍珠似的光。他把麦粒放进嘴里嚼,淀粉的甜味在舌尖漫开,带着点土腥味,和他吃过的所有味道都不一样——是土地本身的味道,是秦汉的雨、隋唐的露、明清的霜,还有他自己淌过的汗,混在一起的味道。
远处的村庄亮起灯,炊烟直直地往上飘。瓷扛起布袋往回走,青铜镰在腰间晃悠,偶尔碰在布袋上,发出轻响,像在跟麦穗说悄悄话。他知道,自己不过是这麦地里的个过客,就像那些被磨平的界碑,被遗忘的农具,被风吹散的炊烟。可只要麦还在长,只要每年夏天,这地里还能飘出麦香,他就不算真的离开。
走到田埂尽头时,他回头望了一眼。暮色已经漫过麦梢,收割机停在远处,像个沉默的巨人。风还在吹,麦浪的声音轻了,像在哼支古老的歌。瓷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布袋里的麦穗互相碰撞,发出细碎的响,像在数:一茬,两茬,三茬……数到最后,分不清是在数麦子,还是在数自己。
夜慢慢深了,他的脚步声还在麦茬地里响,一步,又一步,像在给这千万次的麦熟,打着拍子。




![表情[wozuimei]-拟人圈](https://ch.baicsi.cn/wp-content/themes/zibll/img/smilies/wozuimei.gif) 是独属于农耕文明的浪漫啊
是独属于农耕文明的浪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