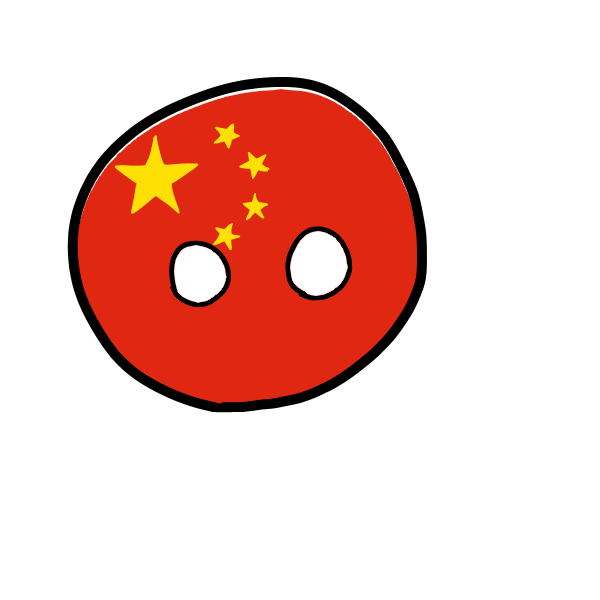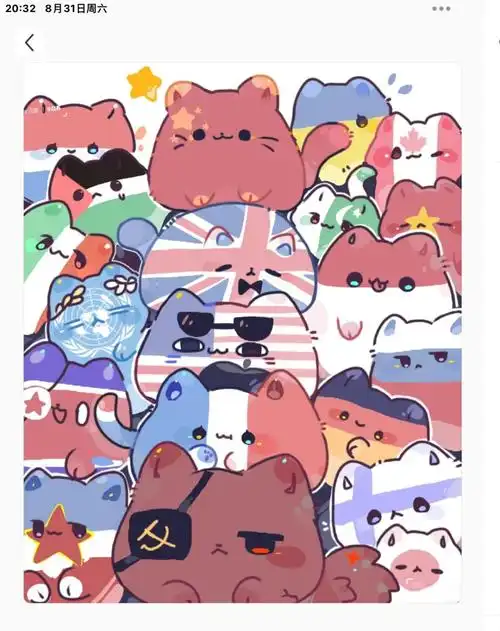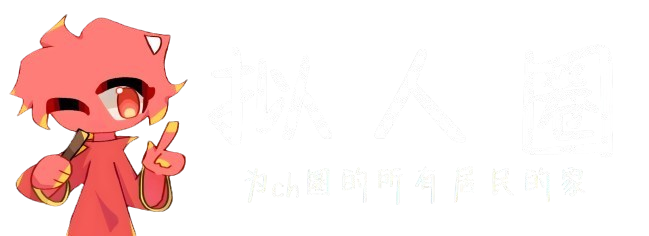欢迎回到以你为名的夏天(共瓷,cb向,微历史向,最后一段半夜灵感来了,现场写的)
瓷踩着延安土路上的碎月光往里走时,远远就看见窑洞的窗纸上晃着个熟悉的影子。不是现在常见的西装革履,是蓝布褂子配黑布鞋,袖口磨出的毛边在风里轻轻掀——像极了1946年那个麦收的午后,共蹲在打谷场边帮他补军装,针线在布上走得歪歪扭扭,却把撕裂的口子缝得比谁都结实。
“灶上炖着羊肉汤。”共掀开门帘时,手里还攥着根纳了一半的鞋底,麻线在指间绕了个圈,“去年冬天从老乡那换的羊,存了半扇在窖里,就等你回来炖。”瓷的目光落在灶台旁的矮凳上,凳脚绑着截粗铁丝,是1947年冬防时,共怕他夜里起夜摔着,特意找铁匠打的防滑链,现在铁丝上锈出了好看的红纹,像串没说出口的惦念。
羊肉汤的热气漫上来,糊了瓷的眼镜片。他摘下眼镜擦时,指尖触到镜腿的划痕——是那年夏天在河边洗照片,共抢着要先看解放区的新报纸,俩人撞在一起,眼镜磕在石头上崩出的豁口。那时的河水凉得扎手,共却把他的手按进自己怀里焐着,说:“等全国解放了,给你配副金框的,摔不碎的那种。”现在的眼镜是钛合金的,轻得很,可瓷总觉得,不如当年那副带着划痕的玻璃片暖和。
“发啥呆?”共往他碗里舀了勺羊油,“快喝,凉了就腻了。”瓷低头喝了口,膻味混着花椒的麻漫开,突然想起那个雪没膝盖的冬天。他们在山神庙里分食一碗热汤,共把唯一的羊油渣全挑给他,自己喝着漂着冰碴的清汤,说:“你得攒着劲,以后要画新中国的地图呢。”那时的风从庙门灌进来,卷着雪沫子打在脸上,可瓷捧着热汤碗,觉得浑身都烫得像揣了团火。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响,溅出的火星落在青砖地上,又慢慢暗下去。瓷盯着那点余烬,忽然看见1948年的夏夜:共举着马灯在前面走,他跟在后面踩脚印,灯芯在风里晃得厉害,把俩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两条拧在一起的麻绳。“过了这道梁就是根据地了,”共回头时,马灯的光在他眼里跳,“到了那儿,给你找块平整的石板当画案,你不是总说在膝盖上画图纸硌得慌?”后来真找着了块青石板,共每天用粗布擦得发亮,瓷在上面画过兵工厂的草图,也画过给老乡家孩子的小人书,石板边缘现在还留着深浅不一的刻痕,是岁月啃出的暖。
“你看这筐里的枣。”共突然往他怀里塞了个柳条筐,枣子红得发亮,沾着新鲜的泥土,“后坡那棵老枣树结的,比那年你偷偷藏在我干粮袋里的甜。”瓷捏起颗枣,指尖的纹路陷进枣皮的褶皱里,像落进了1945年的秋。那时他跟着共去征收公粮,路上见着棵野枣树,摘了把揣在兜里,晚上趁共写报告,偷偷塞进他枕头下。第二天共红着脸把枣核埋在窑洞门口,说:“等它长出树来,就叫‘瓷枣’。”现在那棵枣树早长得比窑洞还高,每年结的枣子,共都要留半筐等着他。
院角的石磨盘上晒着些干辣椒,红得像串小灯笼。瓷蹲下去翻了翻,磨盘边缘的凹槽里还嵌着点玉米粒——是1949年春播时,他们一起磨种子,共说“磨得细点,出芽率高”,俩人推着磨盘转了一下午,汗珠子滴在磨盘上,晕开的湿痕里,藏着“今年要多打三担粮”的盼头。现在的磨盘早不用了,可共还是每天擦得干干净净,说“留着吧,以后让孩子们看看,当年的粮食是咋来的”。
夜色浓得化不开时,共从炕洞里摸出个铁皮盒。打开的瞬间,一股陈墨香漫出来,是半盒1948年产的松烟墨,墨块上刻着个小小的“共”字,是他当年用刺刀尖一点点刻的。“你当年总说这墨发灰,”共笑着往他手里塞,“现在给你磨墨,写幅‘延安新貌’?”瓷捏着墨块的手顿了顿,墨香里混着淡淡的霉味,像那年在地道里,他趴在共的膝盖上写宣传稿,煤油灯熏得纸页发脆,可每个字都透着光。
临走时,共往他包里塞了个布包。瓷摸了摸,是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褂子,领口绣着圈细红边——是照着当年那件打了三个补丁的褂子做的,只是布料换成了现在的棉绸,软得像朵云。“现在不兴穿这个了,”共挠挠头,“可想着你或许会喜欢,就找裁缝做了件。”瓷把褂子贴在胸口,能闻到阳光晒过的味道,像1947年那个晒粮的午后,共把他的军装铺在麦垛上晒,自己蹲在旁边守着,怕鸟雀啄了粮食,也怕风卷走了那件带着他体温的布衫。
车开上黄土高坡时,瓷打开布包,除了蓝布褂子,还有张泛黄的纸。是1946年的秋,他画的共蹲在打谷场补军装的素描,线条被岁月浸得发乌,可共鬓角的汗滴、指尖的针线,都清晰得像昨天。纸背面有行小字,是共后来补写的:“那年夏天,你说‘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我信。”
手机在兜里震了震,是共发来的照片。窑洞的灯还亮着,窗纸上的影子正弯腰给灶膛添柴,旁边的矮凳上,放着他没喝完的羊肉汤碗,碗沿还沾着点羊油,像颗没擦干净的星星。瓷回了条消息,没说别的,只拍了张车窗外的月亮:“明年麦收时,我来帮你打谷。”
车窗外的风卷着枣花香扑进来,瓷忽然懂了那句“人的一生只经历一个夏天”。不是说后来的蝉鸣不够响,也不是说近年的阳光不够烈,而是那个以彼此为名的夏天,早把最真的热、最沉的念,熬成了岁月的底色。像这延安的土,当年埋过他们的干粮,现在长着他们的庄稼;像这窑洞的灯,当年照着他们画蓝图,现在暖着他们等归人。
所谓“以你为名”,从来不是某段逝去的时光。是共缝补的针脚里藏着的“我护你”,是他画笔下晕开的“我信你”;是打谷场的麦香里飘着的“一起走”,是窑洞的灯光里浸着的“等着你”。它不在回忆里独自发烫,而在每个日出日落里长新芽——就像后坡那棵“瓷枣”树,年复一年结着甜果,把当年藏在枣核里的盼,长成了望不到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