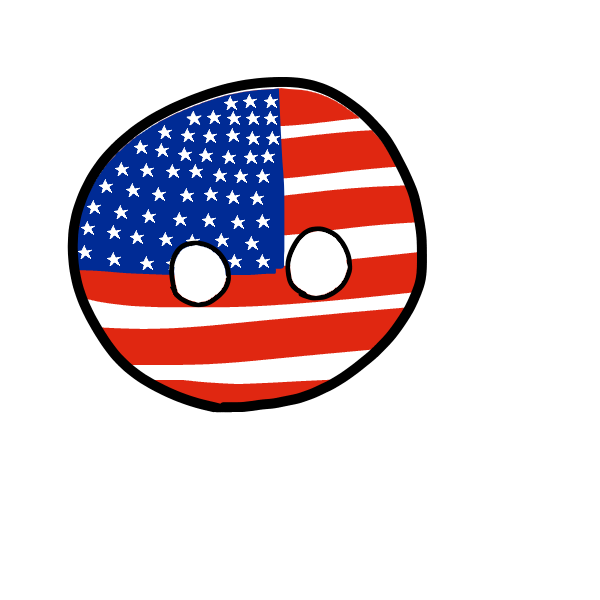当苏维埃映入我眼中的那一刻,我正在思索该如何安置有趋势产生的新政党,大脑接受到视神经传来的图像信息后首先产生的情绪是荒唐,而后判断这准是有谁在作弄我。洛杉矶?纽约?俄罗斯?英吉利?不,这没有任何道理也并不值当。
我没动,保持着原先的姿势看着他,房间的灯极亮足以让我看清他的神态,他用一种安谥的哲学思考式的面容与我一同沉默着,静静注视着我。
寂静犹如一滴乌黑的墨汁迅速在这个房中弥漫开来,美利坚正坐在办公桌前,握笔的手就这么让笔尖悬在离纸面极近的距离上,苏联垂着眼,在强光下像是被降低了透明度一般的幽灵。
——这的确是苏维埃,不可能有人的装得这么像甚至于连那令人讨厌的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气味儿都别无二致。美利坚没表露出来什么表情,冷静得仿佛他什么都没看到似的,正要低头继续做会谈纪要草案时再抬眼,苏联便消失了。
也许这是幻觉,他这般对自己解释。然而内心的平和却不如面部那般好维持,美利坚不得不多番修正他写错的这个或是那个低级错误的纪要。坦自来讲他讨厌工作,因为大多时他几乎看不到工作的意义,但这却生产着那些肠子里燃烧着神圣之火的人的最大的不幸。
喉部传来异样的堵感随之便是鼻塞,血液的温度仿佛只体现在了头以下的身体,听力所感到最敏锐的不是周遭的噪音,而是心脏急促的跳动声。嘴唇发麻尤为明显,而后便是头部胀痛……
他毫无预兆迅速翻身摸向藏在床垫夹缝里的手枪上膛后指向前方。没有人,确切的说他没感到有什么气息。但脖颈处的触感仍旧存在,只是宽松了些,阴冷冰凉,简直不像人类的温度。美利坚睁眼,苏联正在他身前,脸对脸与他保持着极近的危险距离双手掐住他的脖子。那原本暗红的眸色在夜中显出一种深不见底的黑,从地狱爬出找他索命的鬼魂?美利坚想,但这与幻想家所描绘的鬼并不一样。苏联人的胸口能观察到微小的起伏,发丝由于角度原因垂落到他额头上一些,带来细碎痒意。
美利坚放弃了开枪的举动转而调转位置枪托向下很狠砸下来,然而没起到任何作用。手枪穿透苏维埃落至床上被柔软的床垫抵消掉了声响,对方露出一个极具嘲讽的笑容旋即松开手。
“不欢迎我?美国,你的外交就是这么对待人的?”见美利坚开灯,苏联也没动,任他打量着自己。美国人眼珠缓慢移动锁定他的眼睛,发出短促的笑声,“外交可不是给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用的,亲爱的。”
那么你是来做什么的?这儿是人间,苏联,人间啊!他近乎亢奋地说,你要杀死我吗?亲爱的、亲爱的,阿特拉斯正顶着繁星呢,那是命运规则,你杀不死我的!你为什么偏要从地下来烦我呢?真该死啊苏联,也许你该找中国、找俄罗斯,他们或许发发善心会帮你祈祷一下让你去天堂。可我不会,地狱十八层你少下一层我都会难过得从氧气变成二氧化碳。为什——么呢?
“你以为我想在你身边?老实说,是我只能跟着你,在你周围,没有多少可动之处。”
这不是什么好处!棒极了!美国也许会这么说,苏联交到了意外的坏运!再等一天。成千上万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坏运!再等一天…再等一天。不,你还是快点去死的好。美利坚戏谑地逼近他,亲爱的,掐死我啊,为什么不呢?掐死我吧,我也会弄死你哦,你的围巾呢?弄丢了?我发发善心再给你一个吧,你该感谢我…为什么不呢……
苏联十分怀疑美国最近又发动了什么战争,他的状态显然堪忧,美国政府难道连意识体个人是否吸Du都管不住么?为了提高士兵的成力真是不择手段。他想起二战,想起士兵,想起轴心与同盟。都要胜利,都要胜利!于是高层源源不断分发下一粒粒、一瓶瓶、一堆堆白色的化学上瘾性药物,任由粉红的软肉白色的碳酸结构成的坚硬物质咬碎…或许是碾成粉尘,或许是径直吞咽了下去,美利坚可能知道…不,大概不会,高层向来不自己碰这些东西,正如他们为上帝卖命而不为人民卖命一样。但毫无疑问,美国本人受其影响颇深。
美利坚速度很快,苏维埃不得不跟着他一路去到储物室。美利坚现在的热情又是美国人所有的了,看得出来他准备为这种热情构造出一座大楼。他热心地打开储物室的锁像寻找一节肠子那样翻寻着杂物,直到血液顺着红绸流到他手中——代表1987年他们双方关系出现好转的他亲手送给美国的围巾此刻嬉笑般在空气中沉沉浮浮,三十九年……美利坚微笑着……三十九年。偷窃、谋杀、爱情不断开始又终结,虱子拼命地跳叫着歌唱,斗争,痛苦,死亡一直在进行。美国?美利坚?美利坚没什么变化,但又似乎变了一些,像难以观测的行星。技术似乎在逐年崩坏,渐渐再也不可能看清它的全貌,技术……
美利坚步伐轻快地走到厨房,恶劣地对着苏联晃了晃那围巾而后毫不犹豫开火待其底部烧着后将它移了出来,正对着苏维埃,任凭烈火烧血灼人心,火舌在发生在两人之间的默剧中嚣张地缠绕而上。往上、再往上……它被扔至地下继续快活地燃烧,最后徒留下焦黑的、被杀死的、蜷缩在光滑洁净地面上的物质,它尚还有着不成型的结构,只是内部早已破碎掉,一派荒芜。
美国发觉苏联人的身形随着围巾的燃烧一点点变得更加透明,他再次兴奋起来,像刚获得了几枚金币的拉撒路一样欢呼着:“我知道了!哈!我知道了!”美利坚终于真心实意地笑出声,“这样你就会离开,对不对?这样你就会消亡!围巾…围巾……亲爱的Soviet,下一个是什么呢?嗯?”
苏维埃说:“有病就去治。”
美利坚并不理会他这句冷淡的话,他转身上楼回房又关上灯,像个刚被埋下去一小时的死者那样心满意足地躺着、得到了只有在统计学上才会拥有的幸福。消亡!消亡!苏联慢慢把手伸了过去。卑劣、不堪…美国睡了吗?怎么会!美利坚?他长久地凝视着美国,没有任何要醒来的迹象,直至他的手穿透他的胸膛都没有。苏维埃几乎是吃了一惊,他又开始想对方究竟是在做什么梦,1988年的莫斯科之行?四点议程?军控协议签订?86年互相交换新年贺词?…美利坚?你说呢?他俯下身。你到底——
这便是第一天的经过,美利坚决心请了三天假前住前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人员惊愕的询问被他拒绝。苏维埃有意与他保持了一些根本没有任何用的蔓延的、收缩的、橱窗的距离。那橱窗中正出售着梦,一个并不珍贵但平静的梦,所有买下这梦的人都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蛋!它使一切停滞不前,就像2025只是一个幻想,大使馆还在1986年,间谍通过各种手段安假牙一般窃取了各种情报,会晤仍在继续但对他而言政治上的距离则变得更长。热带鱼在鱼缸中游动也许下一秒就会死亡变成一大片酸酸的黑面包。不,这未免也太过离奇……怎么会离奇呢?!你怎么能证明呢?摩天大楼会变成一个发着磷光的尸体,而你则可能是一个自然公园。为什么不可能呢?你不知道只是你没活到那个时侯而已,像原始人类不知道沙子可以变成玻璃那样。基督绝不会再降人世,而人们却还在不停祈祷,神呐…
美利坚不甚礼貌地进了会客厅…不,礼貌这个词早已死亡了,没什么礼不礼貌,这种无聊古老的词汇只会让人们早死,以至于生出的蛆虫啃咬他们的肝都会产生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大使匆忙赶到,美国却早已从一旁的实木装饰架上拿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那个架子恐怕除了那个插着国旗的小瓶外什么也不曾变换。俄罗斯的三色旗取代了苏联红旗,惟有一旁的美国星条旗微笑着无动于衷。美利坚在说什么?也许他是在表达歉意。总而言之他拿到了那个东西,一副黑色的皮制手套。
手套…多么熟悉的事物,竟遗落到华盛顿来了吗?美利坚怎么会知道呢?他想,哦,是出访华盛顿那庆,他将手套落在了大使馆。1987年12月10日,他在华盛顿的第三天,车队向白宫出发时他临时起意要接触一下那些美国人。这是没有任何事先透露的,不可能作戏,于是他获得了欢呼、微笑、握手与祝福。多么难以置信!苏维埃稍稍侧头,就瞥见美国坐在他后方的轿车,歪着头露出一个很浅的笑。
美国现下也在笑,只是连同一起的还有他毫不留情的动作。美利坚向来不是个喜欢蛮力的人,此刻却一点点地、近乎粗暴地撕扯着这只手套,细密的线开始崩裂,还有什么进行时呢?野牛群正在绝种、奥丁正在失去对世界的统治权、印钞机仍在工作、罪恶仍未断绝,他自己也在逐渐更加透明。荒谬的世界!只有美国能看到他!只有美国!只是美国!有条不紊的昏庸,该死的世界!美利坚开始拿另一只手套……刺啦…锃亮的菜刀下响起牲畜的尖叫…刺啦。一个男孩被炸香蕉杀死…刺啦……刺啦…
手套彻底地被破坏,美国将它们的残骸投进河里再也不看一眼,去他妈的环保,你们这些环保组织简直像一个跳芭蕾舞的大象那样不可理喻。他瞧向苏联,估摸着再有一次他就彻底摆脱他啦。美利坚上车漫不住心地思索下一个物什该是什么。
“我之前没看出你如此恨我,”苏联人显出一种奇怪的坦诚和困惑,好像他刚把奥伯龙这个向导弄丢了似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是社/会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思想?”
“听着,我不会因为制度不一而恨一个人,从不!至于思想——苏联,你真觉得禁止、恨有用?思想是消灭不了的,它像蛆、蚂蚁一样从枯树中爬出来,充其量也就是讨厌!讨厌!”美利坚咬着牙重复道,不知哪句话触到了他的神经,他怒不可遏,“太可笑了,苏联!我可以和你说明白,当初你要进行政治变革要和我改善关系,我不反对你懂吗?!我也可以接受我们两个共同裁减军备,我们可以合作,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你说我是战争贩子、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算在苏联头上,可你呢?
“你们的战斗机击落了一架偏离航线误入苏联领空的客机,二百多人死亡。你否认这与飞机失事误入领空有关,声称我利用韩国的民航客机作为间谍飞机,我应对此负责。之前难道没有类似的事件吗?但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伤亡也远小得多,你却将它演为了外交对抗。
“你派间谍来我这儿当雇员,这件事我是有确凿证据的。而你们、克格勃试图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你们抓了一名没什么名气的美国人,捏造罪名指控他迫使我释放间谍。好多次都是这样,好多次。”他说,“后来我所支持的政策有利于创造你解体的条件,我想这不用我说。这才是我恨你的原因。”
“……”
“好了,我不想再讨论这种没意义的事了。但我有了个想法,在莫斯科。”他满怀恶意地笑,“你马上就可以去死,马上。”
这句话是由一串果胶星星在夜空中散发的银白冷光所组成的波纹无生命物质,阴沟污水结的冰冻住了一只死猫。太阳在白日散发出寒冷的白条月光约拿坐在鲸鱼的肚子里胡言乱语声称也许它在未来会变成月亮,生命是冰冷的美元,在一刻不停地为欲望大吃大嚼,像癌一样成长最终死于食物不足。它们如此吵闹甚至于耶稣本人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艾尔.卡彭都难以忍受。上帝也许建立了新的天堂、新的人间、新的耶路撒冷……第一个天堂与人间早已消失,该隐和亚伯业已死亡,一切都在开始,快结束吧……快结束吧…缠丝玛瑙构成的“生命水之河、狗屁不通的语言文字……明天即将到来,一切都为了明天,但明天永不到来……快结束吧,你愚蠢的精神上的毛病……美国手指向窗外一指:看,谢列梅捷沃3号。苏维埃不必看便知晓他在说红场,这个挖苦性的称呼随着赛纳斯的降落无疑也揭开了防空的漏洞,西德飞机的到来使它被取笑为了一个国际机场。从S到O,再到那个数字3,这是一种纠缠不休的耻辱形成的漫长字母的郁积。从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于人口到现在又被美国旧事重提的那个漫长的年月就好似亚瑟王传奇中的一段叙事诗,洪水已然退去,洪水从未褪去,耶和华却仍为诺亚降下无数次吩咐,方舟在坟墓中漂行了几十个一百五十天……快结束吧…莉莉丝将给你炼制最致命的女巫毒药……
俄罗斯显然不满于美利坚大半夜的叨扰,但还是耐着性子扮演着一个类似律师的职业了解他那一美分都不会付给他的雇主的诉求。苏维埃希望自己能够摆脱于他们俩的谈话,然而这似乎是一种星尘团橱窗中放置的奢望,比世界上任何地点都遥不可及——手枪?Pistol?美国方才是说了这个词。
俄罗斯皱眉,他可能以为美利坚没睡醒,“你要那东西干嘛?可别跟我说是睹物思情,我记得这枪的子弹有次误射中你了还是你自己边吐血边抠出来的。”
“不是,但总之你留着也没用,占空间。”他言简意赅,俄国人瞧了他几秒后转身回屋找去了,片刻后丢给美国半袋子弹和用塑料袋封证物似的保存着的手枪。他站在门口也许还想说句狠话来报复这个半夜把他从床上叫起来的美国佬,最终憋了半天,关上门。
美利坚冲苏联扬了扬手中的东西,只是没有笑。苏维埃的子弹是被要求定制的,每一枚都有他本人的名字——Soviet,舌尖向上,先是轻轻落在门牙上、下嘴唇而后又回到上颚。苏,维,埃。Soviet。肺部传来阵阵幻痛。铁锈味是活着的,毫无凭介地在口腔中四散跑开,在分子原子的运动中窜入空气,连呼吸都是冷冽的疼。
美利坚在返程的途中面无表情,连讥讽都没说过一句。苏联暗想美国就是这样,他在达成目标前往往不会吝啬自己外泄的情感,为什么不?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讲他的情感太过丰富,足以把自己推下深渊熨烫漂浮摧毁理智,疯子就是这样的,当然,美国可不是个疯子。他有一种愚蠢到不可救药的聪明,苏维埃不确定美利坚是否认为他也有,但显而的——不可救药…美利坚开了锁,又从杂物间拿出一种小型机器。苏联闭了闭眼。
事实上,美国的确就是这样,每当接近他所渴求的答案时他反而冷静地像一块钢筋混凝土,而在凝固之前它尖叫着放热、释放热量、热情。你若被它蛊惑你便完了,它会吞掉你整个人,就算不是整个也必定教你失胳膊断腿屁滚尿流才罢休……在他思索的空当,美国早用铁锤将那手枪砸了个稀烂,碎片零落在平滑的地面上。美利坚并不在意它们,只是当着苏联的面将刻有他名字的子弹一个个丢进融炼炉中。早已在上世纪未消亡的人就这样悲哀地望着他,美国在新的世纪中如同一位雕刻家耐心地雕刻着自己的作品一般耐心地、一点点地再次毁灭早已被他杀死的人。
直到最后,苏维埃的身形已几近透明,美利坚惊觉发现这时候他反而可以碰到他了。他捻着最后一枚子弹起身,拽着苏联的手将子弹放在他的掌心而后放任它滑落进炙热的毁灭中。
“回你的地狱呆着去吧,苏联。我恨你 就是这样。”
“你也会去的,”苏维埃盯着他,声音阴冷而遥远,“我在地狱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