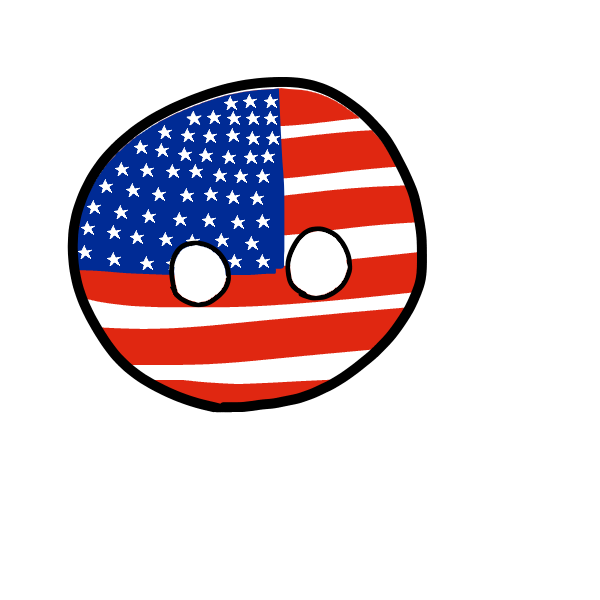有点兴致,但不习惯用。
在又一次拂了英国面子后,英吉利平静地瞧着美利坚,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当初以为你不会那么快和我重新建立友好关系。”
“什么?”美国愕然。
“你刚独立那阵子。”
英格兰那座岛上雨总是连绵,往往悄无声息地沾湿你的发梢、衣间,英吉利也习惯了这种天气,就连在外逢小雨也只是疾步快走。
“雨没大到要撑伞的地步。”
十三州想这恰恰是最令人讨厌的一点,这雨毫无犹豫地砸在他身上同他的身体无可避免产生了联系却又不肯将他透彻的淋湿,斑驳的衣服仍旧挂在身上,深深浅浅。
他会扔掉这件衣服的,十三州神情有些厌烦,他的确这么做了。衣橱中的衣物还算多,丢掉一件不是什么大事。坦白来讲英格兰庄园内部布置得复古舒适,不同颜色的美丽彩窗总和房间饰物的色调保持协调,只待光线日复一日映射出它们那空幻的绚丽斑斓、光怪陆离的效果。但他现在打心底讨厌这儿,每月来住的一周更是可恶至极。
一切的一切,十年也未曾有多大改变,会客厅小桌上的《哈姆雷特》被来往的客人随手拿起又放下,第二天仆人又将其细致地校准回原应的角度、方位;苦涩的茶味总在下午某一周定时间孤哀凄寂如怨魂似的丝丝缕缕缠绕在他鼻间。英国的庄园每日都会有人将所有房间细细收拾过一遍可不知怎的,每逢他一触碰总有一种腐朽雨后的霉味儿。
英吉利这儿不像会有这种味,十三州觉得北美大陆上才有符合这印象的房屋,那些最早期英国殖民者们留下的失修无人的年久的木屋,世世代代下去早已被弃用,最终无可奈何在树林深处象征一声古老的呻吟。
他着实厌倦了这儿,厌倦那片阴雨连绵的土地,厌倦了一成不变的位置摆放连带着厌倦了英吉利,这地方没有欢乐,哦,冷硬的沙壤。但毕竟面对英国时不能表现出来,熟练的微笑不用谁说也慢慢变得完美无暇,他并不胆怯,千百次如一地注视着英国的眼。
英吉利稍顿一会,而后略略侧过头去。
英国、英国。
他第一个认识的是英国、陪伴时间最长的是英国、对他意义最深的是英国、他的灵魂意识在一片苍茫混沌的最初也来自英国。可也是英国,如此不公平地对待两个同在北美的殖民地。先是《皇室诏谕》不准他移入拓大新的土地,又公布《魁北克法案》宽松以治,加强加拿大魁北克的地位。就是那一年,1774年,他不再每月去往英格兰,十三州愈发憎恶那个国度,它如此遥远又近在眼前,带着点儿来自地狱的安洋味道。
新诞的合众国静静地凝望着杰斐逊认真起草那篇即将斩断他同英吉利联系的宣言,墨水随着分分毫毫变化位置的日光缓慢渗入纸张,这真是个奇妙的事情!就在不久,几乎是方才,他在一笔一划中出现在这房间并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名字。不错,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是潘恩所提议的。
杰斐逊显然未曾经历过国家意识体诞生的场面,这与传闻并不相同,至少与欧洲那些国家间的传闻不同,没什么异象的大动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托马斯吃惊地低头看向自己方开完一个头写下“美利坚合众国”的草拟文件转而又抬头小心打量着对面的人儿,半晌迟疑地问,“您是我们新的国家的意识体,对吗?”
美利坚点点头,这位新生的国家看上去并不康健,面色苍白又略带些不正常的红,肩膀处于一种咳嗽与不咳嗽之间的轻微颤抖,略露出的左手袖口处有一块淡红色的痕迹。杰斐逊犹豫着询问是否要为他叫来一名医师,美利坚拒绝了。这没什么可瞒的,他告诉杰悲逊,之所以会是这样仅仅是因为独立的重要文件还未完成,不过不必着急,这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光阴格外地漫长,一时间只能听到沙沙的写字声响。杰斐逊先生无论是英文字体亦或文采都十分不错,现在正认真地就着草稿进行润色,他有些出神,在想英吉利将会是什么表情。
失望?愤怒?不可置信?……不,肯定不会是。英国那样一个人,不可能会表现出这种情绪的,他虚伪、冷漠、重视于那装腔作势的做作礼仪,也根本不在乎除自己之外别人的死活。美利坚不介意就他自己的实例大做文章,事实上已经有人替他这么干了,他没想出英吉利究竟会做何表情,最后不耐地用舌尖抵了抵牙,忽而才想到他现在还未独立。
实质、名义上还未,美利坚看了眼那位可亲可敬的认真先生,想,不过也快了。他在几周前尚还叫英国父亲,短短时问内这一百多年来的习惯称呼被他如此迅速改掉,自然这也不值得什么留恋。“父亲”这个对待宗主国的称呼源故也不知自何而起,但一定的,在最初的开始一定有殖民地诞生后在茫然无措中犹豫豫地唤了一声,从此定性了这个关系的这个称呼。加拿大一次曾对他说他称的那声父亲听来总像很散漫似的,在听了几次他人的语气之后他承认的确有些。但Father,Daddy,这种词汇的语气掌握他不太喜欢,反正英国也没说他什么,他索性也就没改,就这样到现在。英吉利估计是懒得计较这种语气问题,平常也只将眼尾向上一挑罢了。
“我要去军队。”他泛不了地冒出来这么一句,独立必有战争,这是可预见的。合众国请求着愣望向他的杰悲逊,“可以吗?并且我希望不要透露我的身份。”
“亲爱的孩子,这我可拿不准,你该问问华盛顿阁下他们。”杰斐逊注视着年轻的祖国,答道。
在7月7日,独立宣言发表过后的三天,这件事经过严肃的讨论后被同意,美国谢绝了送别即刻去了波土顿。当然,他无疑清楚自己现下军备的落后,因此对于军队并未抱什么大希望,他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军官之类,自然也不会横加指责,仅仅打算成为或熟悉成为一名兵士。
同他最快熟络起的是叫马特洛克的一位年纪长者,具有着后来美国人最早的,也是被一些欧洲人所厌恶的乐观品性。马特洛克通常会在训练后的闲暇时间里天南海北的和一些年轻或是同辈人谈论,只要他们能想到,随便什么话题。某次他们怀念起了自己的故乡并要求每人都分享几句,美国认真地在听,却忽然察觉大家都看向他。马特洛克说:“嘿,哈德里安,小伙子到你啦!”
哈德里安,他随意编造的化名。美利坚茫茫然起身,认真思索了一番这个概念后还是摇摇头。“我不知道,我没有故乡。”
众人哄笑起来,坐在马特洛克左手的与他同样年长的伍尔夫也在微笑。“不必紧张,”他安慰道,“想一想,小兄弟。故乡,你生命最初的开始,你生长熟悉的地方,无论何时都会让你有依恋的、与你灵魂联系在一起的地方。”
“美国。”他最终很抱歉地说出了这个令人十分扫兴的答案。
哈德里安?你在这里做什么?
哈德里安?
同一地点,不同时间,马特洛克微笑询问他的面孔在虚幻中扭曲又消散不见。美国坐在河边,又狠狠用粗糙的布条磨着左腕那一小块皮肤,那里俨然快要磨破出血,呈现出发肿的嫣红。“我恨英国,除战争外,我不想再同他产生哪怕一粒沙子那么大的联系。”他听见自己几天前这般回应马特洛克对他的提问。可是…英国,英国…他早该发觉到…英国自他诞生那天就出现在他左手手腕上的淡红色痕迹和英格兰的地图形状别无二致…英国……闭嘴!该死的我知道这和英吉利有关系!…英国……
他的大脑一刻不停地警醒着他,美利坚竭力将注意转到那片红痕却以失败告终。去不掉…去不掉他绝望地想,去不掉。那片红肿的地方已然出血,被冰冷的河水一冲借着月光显出比其他皮肤更深的色彩。无疑,那块淡红在他主人的拼命去除中变为了一种嘲笑般的鲜红、艳红,哈迪斯没有掌管好他的火焰,以至于使它烧到了人间。
美利坚死死地盯住红痕,摩西和各种预言者正在对他讲话,也许上帝的声音也穿透其中,这使一切冲动麻木。他憎恶地捡起地上放了许久的绷带,起身冷漠地将其缠了厚厚的几层在手腕处,直到他一点儿也瞧不见那已刻在他心里的红痕。动作之迅疾仿佛宇宙正在凝视他手腕赤裸裸的标志一般的图案似的。
他走向营处,夜中有着微小的呼呼风声——这常被人们猜作女巫与撒旦乘风掠过天空越过居留地和孤寂的农舍时发出的声音。
美利坚慢吞吞前行,沉吟着。缠绕过紧的绷带下的伤口痛感顺着神经连绵不断地爬入脑中,迫使其清醒了些。与法国结盟后他们的处境要好上不少,援助应当也快要来了………这和英国脱不了干系,莫非是还在独战的原因?…那些法国人倒也不错,没有英国所说那样轻浮、畸形……脑中的思绪仍杂乱纷飞,像刚被吹过、四散纷飞的缎带。
好吧,好吧,那不打紧,战争总会见出分晓,他会赢的,他也的确赢了。固执的英王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这场战争,英国承认了这场独立却在同时立即宣布以后美国货物来英国同等加税。自由的小代价可以不计,曾和他是战友的法国人和他的人民得知他后意外地更与他亲近起来。社会需要恢复,法律需要进一步确定,异邦人休养过后十分不舍地打道回府,但海洋两岸信件来往仍旧密切。
然而一切总有不顺,左手的淡痕像鬼魂似的阴魂不散的提醒着他。战后汉密尔顿主张与英国减少联,华盛顿则更赞同于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美利坚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当他真正成为一个国家意识体时便会轻而易举地发说他本身的私人情感将会是一种必要的忽略物,作为他这一身份也必将从长远角度出发,无论政治、外交、经济,没有什么以私人决定的,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美利坚临时要求出去一会儿,长者们没有多问便同意了他这个请求。这处的地址稍有偏僻,几十步开外便是可见一片树林,他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不着边际的思绪之中。还未独立之时他便常毫不胆怯地注视着英国的眼,年长者大多时候会刻意控制自己不去看他。英国人的眼睛是森林一般的绿色,这常常让他联想到在森林中摇曳而又忽然阴晦的阳光,地上铺平了柔软的落叶,空气总是清新就像年幼的孩子总会误以为森林是生命长青,而那儿必有一堆繁茂的苔藓或是什么别的叫他们曾经喜爱的东西。
英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大概就在于眼睛,有人对美利坚说过他的眼睛很好看,淡蓝色的,像反射着光的小溪。美利坚喜欢这个比喻,你总是能在森林中瞧见小溪,铺着鹅卵石的棕色沙子的河床,从神秘又似乎可见一斑的泉眼流出,静静地向前流淌,心里荡漾着有关森林的色彩暗淡的事件,随后,它流出森林。
英国,它总会流出森林的。
小溪总会流出森林的。
他忽而笑了起来,俯下身亲吻这片土地。哦,湿润的;哦,混合着生机的草木味儿的!这儿和那儿共同构成一个名为故土的牡蛎般的名词。尽管异拜的那片没有欢乐,他也毫无疑问地厌倦了那儿,可那有什么要紧的呢?一切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毛病都不是主要的,故乡带来的魅力一直存在以至于亲英派仍旧猖獗。最早的殖民者,那些原先的英国人出现在这荒无人烟、森林环绕的土地以来已有一百多年了,贫瘠的土地发展成了村落,又成了城镇,也许在一定的将来还会成为繁华的都市。原先英国人的后代在这里诞生又死亡,他们世俗的物质肯定的与这块土地交融在一起,直到有相当一部分土地与其有了血肉关系。盎撒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错,这正是他的血液、血统,乃至全身的组成!这种长期联系的本能也许永远使他保持着与英国的联系,随着历史永远像一根深深扎下的文雅的尖刺亘古不断无可避免无休无了地令他意识这永不可能将他同英国断绝!
英国……他念着,又笑起来,手腕的绷带不知何时脱落下来,露出一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