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吉利的手钳住了他的腕骨,像毫不费力地捏碎一个过分成熟的苹果。
指节爆出青白,“咔”一声细微的骨裂被淹没在更响的、什么东西碎裂的动静里。剧痛是锐利的,但他此刻竟有些麻木,只觉得肚腹深处传来一阵无法承受的绞拧,仿佛一柄钝刀残忍刺入,翻搅不休。
孩子就是在那一刻没的。
这个被寄托了太多名字的小生命——政治联盟最终见证的王子、亚瑟,或是其他任何代号——在那个瞬间灰飞烟灭。尖锐冰冷的痛楚如瀑布从头顶猛然冲下,流遍他全身,也带走了体内唯一温热的希望。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在瞬间冷透、干涸,只留下空旷和无穷无尽的绞痛。剧痛与骤然的虚空感令他眼前发黑,温热的粘稠液体无声地沿着腿内侧急急滑落,浸透了丝绸布料,迅速在地板蔓延开来,映出冷硬的倒影。
“法兰西……”英吉利的嗓子里哽着一团灼热的焦炭,手劲却在瞬间泄了。他的手指依然停留在法兰西被他捏出紫淤的手腕上,可那力道突兀地化为虚脱的绵软,只留下灼烧般的触痛痕迹,如同刚被剥去一层皮的印记。法兰西能看见那张曾因狂怒而扭曲的脸孔一点点抽离了血色,暴突的血管悄然沉寂下去,徒留一片惨白底色。
他甚至没有气力栽倒。小腹深处那阵凶猛的攫取绞拧过后,一种突兀的虚空取代了所有剧痛。身体里被硬生生拽出去的,似乎不仅是什么温热的存在,还有他所有的气力。他靠着墙壁一点点向下滑落,动作迟缓僵直仿佛机器失灵,视线里英吉利沾着猩红的手指在自己身下不断晕染开的那片潮湿上徒劳抓握,仿佛溺水者无力的挣扎。法兰西盯着天花板上繁复的纹饰,视网膜上残留着方才英吉利挥拳砸来的凶戾。那个拳头曾带着席卷一切的飓风之势撕裂空气,目标就是他的小腹——孩子所在之处。却不知何故,最后一刻猛地偏转了方向,化作一声巨大震响,在墙纸上砸开一个丑陋无比的破洞。飞溅的碎屑像惊魂未定的苍白雪片,落在那片殷红滑落的路径上。
“血……”英吉利的声音扭曲变形,像老旧破风箱里挤出的惊惧与茫然,那双眼凝固在法兰西腿间缓慢扩散的深色湿痕上。他半跪在地,慌乱地试图用自己的手去堵住那不断溢涌的潮湿暗流,然而鲜红却不受控制地顺着他发抖的手指尖向下滴滴答答,砸在冰冷的地板发出沉闷绝望的声响。法兰西半躺在地上,无力地抬眼看他,腹部的抽搐渐渐平息,只留下无边无际、令人作呕的冰冷虚空。疼痛褪去之后,一种彻底的虚脱攫住了他,身体沉重得像灌满了铅,意志也彻底消散。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粘稠的液体依旧在缓慢涌出,无声宣告着一个事实:那个曾在他身体里孕育的生命,那个维系着他们之间某种扭曲平衡、又让他们彼此都短暂生出期望的生命,彻底消失了。
“……他没了。”他极轻地说出这句话,声音像是被那地板上蔓延的深红吸附了力气,飘渺到几乎听不见,更像一句说给自己的呓语。说完,眼皮沉重地缓缓合拢,无边的黑暗涌来。
再次睁开眼,他最先感知到的是医院特有的刺鼻气味——强烈而冷漠的消毒水气味,混合着某种难以辨识的苦涩气息。随即,视线里是令人眼花的白:惨白的天花板,洁白的墙壁,素白的被单裹着他,像是把他封进一个白色寂静的坟墓。空气冰凉凝滞,一丝风也无。身上盖着的薄被轻若无物,却压得他沉重窒息。身体的每一寸都充斥着虚脱的疲惫,小腹深处残留着酸涩隐痛,仿佛被彻底掏空后留下的无尽空洞。
有人在他身边动了动。英吉利就坐在病床边那张狭小的椅子上,庞大的身躯在这片纯白中显得格外突兀,姿态却僵硬得像个雕塑。他一只手还紧紧握在法兰西那只没受伤的手腕上。察觉到法兰西醒来,英吉利那双灰眼睛立刻转动过来,紧紧锁住他的目光。
“……醒了吗?”英吉利的嗓音异常干涩沙哑,像是刚吞下了一把粗糙沙砾。握着法兰西手腕的指尖似乎微颤一下,却又迅速收得更紧,那感觉几乎快成为骨头的一部分。
法兰西没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英吉利。那双灰眼睛里布满了鲜红的血丝,眼下的乌青深得像化不开的浓墨,胡茬在他惨白的脸上肆意刺出,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种极其古怪的氛围中——既有毫不掩饰的困兽般的疲惫,又诡异地流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狂喜期待,像是在深渊边缘看到一线微光,明知是幻影却仍不顾一切伸手去抓。这怪异而强烈的情绪凝结在他眼中,让法兰西心底涌起一股冰冷的寒意。
“孩子呢?”过了许久,法兰西才开口,声音微弱却清晰,冷冽如同寒风中的薄冰。
英吉利脸上的每一根紧绷的线条似乎都因这两个字轻微跳动了一下。他眼底那种炽热的狂喜瞬间凝固,闪过一丝狼狈的痛楚。
“孩子……自然没了,”他避开了法兰西的目光,盯着雪白床单上细微的褶皱,声音低闷:“医生尽全力了……没办法……”他顿了顿,再次抬起头,眼神专注得令人窒息,声音里带上一种极端的迫切:“但这不重要!‘法兰西’,你听我说——”他握紧了那只没受伤的手,“我们才是最重要的!没了那些累赘的羁绊,只有我们两个了……我可以好好地爱你,用最纯粹的方式!像最初那样!”那语气几乎像在狂热地宣布福音。
一股强烈的恶心感翻涌而上,冲击着法兰西的喉咙。他把头偏开,目光落在自己另一只裹着石膏和绷带的僵硬手腕上。那里的骨头被轻易捏碎,如同踩碎一只无关紧要的枯枝。
护士推门进来换输液瓶,动作利落。她的目光快速扫过英吉利紧攥着法兰西不放的手,又移向法兰西苍白异常的脸,眉头不易察觉地紧皱了一下。
英吉利的视线像钉子一样追随着护士,看着她熟练地更换液体瓶,又测量法兰西的体温。病房里静得能听见药液滴入软管的声音。护士终于完成了例行工作,准备转身离开。
“等等,”英吉利突然出声,声音不大,但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护士停下脚步,看他。他依然握着法兰西的手腕,姿态却略微前倾:“他需要……休息,”英吉利斟酌着词句,目光锐利地盯着护士,“我是说,现在、未来很长时间,他都需要安静。他需要完全恢复,任何打扰都不行。明白吗?”那温和的语气下,隐藏着不容置喙的钢刃,每一个字的强调都透着无形的强硬。
护士抬眼,目光在英吉利脸上短暂停留一瞬,又很快垂下,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明白,先生。”她声音平板地回答,“我会告知其他医务人员和访客。”
“很好。”英吉利满意地点点头,嘴角细微地扯动了一下,但那笑意未达眼底。
病床上,法兰西无声地听着。每一次呼吸都小心翼翼,腹中依旧是一片空洞冰凉,仿佛身体深处被永久地剜走了一大块。那曾孕育的温热、那轻微的脉动,连同他拼尽力气维系的一丝希望,一同化为冰冷的虚无。
护士离开的脚步在空旷的走廊回响。房门轻轻合拢,隔绝了外面的世界。英吉利仿佛瞬间被那轻微的关门声抽去所有力气,先前强硬挺直的肩膀陡然塌下。
“法兰西……”他俯下身,将那只紧握手腕的手抬到唇边。温热的呼吸扑落在法兰西冷冰冰的皮肤上,接着是一个滚烫、带着潮湿的吻,印在石膏边缘露出的几块狰狞青紫上,一遍,又一遍,小心翼翼,近乎膜拜。最后,他的额头抵着法兰西那只完好的手,灰蓝眼睛里翻涌着复杂的暗流——那里面有真切的、带着余悸的后怕,有压抑到变形的痛楚,更有一种扭曲偏执的占有欲在疯狂燃烧。“对不起……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巨大的……”他喃喃低语,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灵魂深处艰难挤出的忏悔,混杂着惊惶与固执,“我们忘掉它,一起忘掉它!就当是……命运的一个警告,让那些不必要的枝蔓彻底消失!”他猛地抬起头,眼里的脆弱如同假象一闪即逝,瞬间便被某种决绝的决心取代:“从今往后,我绝不再碰你一下!我发誓!但你也……别再用那种眼神看我,别再说那些可怕的话威胁离开!我会失控……你明白的,法兰西?离开这个字眼,会让我变得不像我自己!我们必须待在一起,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活下去!只有你和我……足够了!这世上没有比亚瑟更重要的——”
他猛地截住话头,眼底掠过一丝被烫到的痛楚。这个名字在病房的寂静里尖锐地悬停,宛如一道无形的血痕撕裂了他们之间短暂伪装出的平静。孩子死了,那个被寄予所谓未来意义的孩子没了,而他的父亲却在此刻疯狂强调他的重要——何等讽刺的墓志铭。
法兰西闭上眼,不想再看他。那片消失带来的虚冷与疲惫重新覆盖上来,如同沉没在黑暗冰冷的海底。
从医院回到那座冰冷庞大如同陵墓的宅邸,已有四个月光景流逝。手腕上的石膏在回家后的第一个月就已拆下,细瘦的腕部显出不自然的弯曲,像被强行拗折过的脆弱枝桠,活动起来总带着别扭的生硬和细微的疼。每次他试图用那只手做什么,那隐约的痛楚就如同沉默的低语,提醒着他那个不堪的时刻。
初时几周,英吉利谨遵他的诺言,将一种近乎刻板的疏离包裹在自己周身。他出入房间都像一阵刻意减弱的风,走路刻意踮着脚尖放轻脚步,视线总是在触及法兰西的那一刻立即巧妙地滑开,仿佛多看一眼便是天大的冒犯。
然而这层小心翼翼的纸壳被日复一日的寂静渐渐压得变形、皲裂。英吉利的眼神像失去校准的探针,开始不受控地黏着在法兰西身上。那目光里最初残存的一点惊悸畏缩,正被一种更为复杂的、无声燃烧的东西缓慢吞噬,并重新凝聚成型。
像这个午后。
法兰西靠在他常坐的窗边长榻上。阳光透过高而窄的窗户射入,光柱中悬浮着微小的金色尘埃。他有些困倦,但并未入睡。英吉利悄然无声地在他身边坐下,靠得极近,身体的热量隔着衣服布料传递过来。
法兰西没有动,甚至连睫毛都未曾颤一下。心却在那无声的热源靠近时,骤然悬紧。
英吉利伸出手,带着一种信徒般的庄重和无法抑制的虔诚,手指轻轻地、缓缓地落在法兰西的鬓角,小心翼翼地描摹着那清瘦的侧脸轮廓,最后停留在线条精致的下颌边缘,微微摩挲着下颌线上细腻的皮肤。他的手指带着一种奇异的热度和细微的颤抖。
那只手犹豫了片刻,终于像解禁的蛇般游移向下,带着不可置信的温柔,轻轻落在法兰西的后颈上。这个动作本身是轻柔的,法兰西的脖颈却如同被无形的电流击中,瞬间激起细微但令人不安的战栗。他能清晰地“听见”自己颈骨在那一瞬僵硬起来的微响,身体的每一丝肌肉都在那一刻绷紧、无声地抵抗着那只手的重量和温度。后颈的皮肤似乎还记得曾经的剧痛——喉骨被粗暴扼紧的记忆在此刻猛地苏醒,即使再如何轻柔的触碰,也激活了潜藏在骨髓深处的警报,那瞬间激起的窒息感几乎化为可触的实体。
英吉利的手微微僵住了。似乎察觉到了法兰西身体里爆发出的无声警告,那只手迟疑着,却并未移开。他的手指在法兰西后颈绷紧的肌理上停滞了片刻,最终仅以指腹极其轻微地搭着皮肤,勉强维持着一种虚弱的连接。他侧过头,将嘴唇轻轻抵在法兰西的耳际,炙热的鼻息拂弄着法兰西耳后细小的绒毛:“原谅我……我会克制……”他嘶哑着低声说,话语里是痛苦和挣扎的痕迹,可身体依然顽固地紧贴着法兰西,未曾退开分毫,“别离开我……法兰西……求你……”
耳际的灼热气息如同无形的丝线缠绕过来。法兰西的目光空洞地落在远处壁炉冷硬的大理石花纹上。喉结在他的颈间难以察觉地微微滚动了一下。
他颈间环绕着一圈冰冷的金属——那是一条细细的金链,做工精巧,像一件无足轻重的首饰。可它冰凉,紧贴着他颈部最为敏感、最为脆弱的部位,像一道无形的圈禁枷锁。链子上端隐匿在法兰西的发梢之下,那里曾被手指狠狠扼住,留下永久不退的青紫淤痕。现在,金链巧妙地覆盖其上,如同精心设计的遮蔽,锁扣就在他自己的指尖随时可以触到的地方。
链身细细的、却异常牢固,每一节都紧密咬合。链条在靠近锁骨的位置向下延伸,穿过法兰西衬衫严丝合缝的最高那颗纽扣孔,像一条冰冷的银色溪流,最终垂入法兰西胸前最贴身的衣物深处。那里悬挂的坠饰则被他紧紧攥在手心,始终藏着——那是一个冰冷的、小巧的银铃,精巧得令人心碎,内里没有铃舌敲击。它本该系在婴儿的襁褓摇车上,发出清脆笑声的,是那个永远未能踏出产房的小王子。
它是离开医院那天,护士悄悄塞给他的。当冰冷的小东西落入他掌心,她嘴唇无声翕动了一下,眼神带着哀痛与恐惧:“……先生,请保重。远离……远离危险。”
“法兰西……”英吉利的声音带着微颤,又在他耳边响起。握着他手臂的手指倏地收紧了些,像是在抓一块随时都会融化的脆弱冰块。
法兰西的手指下意识地蜷紧了几分,将那沉寂的银铃更深地包裹进冰冷汗湿的掌心。冰冷金属硌着他微凉的掌心皮肤。
英吉利的手指再次触碰上他的颈侧,指尖轻轻压在那条冰凉的金链上,沿着金属的纹路来回摩挲,动作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病态依恋。法兰西的喉结轻微地滑动了一下,颈动脉在薄薄的皮肤下急速跳动,敲击着冰凉的金属。身体内那刚刚平复的寒意又开始无声地弥漫,像地下涌出的冰水,无声地将包裹他。窗外投进的温暖光线明亮刺眼,却照不透他心底逐渐冻结的冰层,那冰层下封冻着他永远失去的温热存在。
法兰西始终沉默着,像一个没有生命的美丽容器。颈链环住的喉咙绷得僵直,指尖紧握着的袖珍银铃死寂无声;链扣在皮肤上若隐若现留下烙印,犹如一种沉默的刺青——记录着以爱之名缠绕的绳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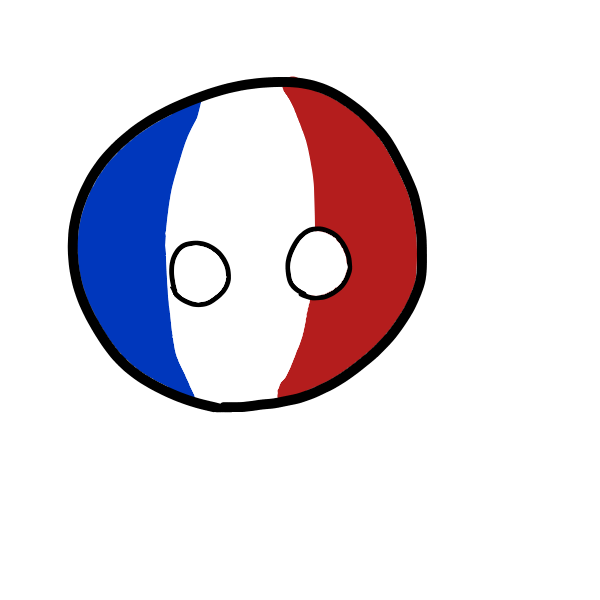


没有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