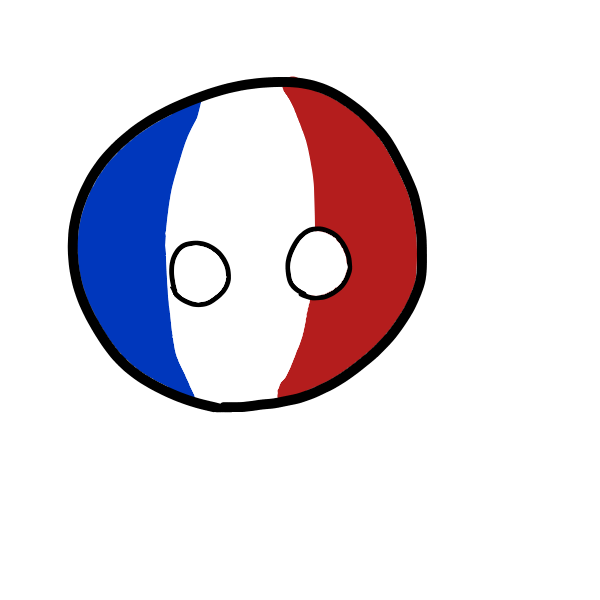掌心下,一阵有规律的、充满生命力的脉动传了过来,仿佛遥远彼岸传来的鼓声,敲打着他的骨肉。每一次胎动,都在法兰西冰封已久的心湖上惊起涟漪。只是这涟漪深处,却沉淀着冰冷的记忆碎片。
上一次这样清晰的胎动,属于那个永远没能见光的亚瑟。这个名字像一根烧红的针,猛地扎进法兰西的神经。他闭上眼,那片记忆深渊瞬间将他吞噬。
冰冷光滑的大理石法庭地板。刺眼惨白的吊顶灯光。空气里凝固着无望的窒息感。他面对着法官,最后一次申诉离婚的理由,声音干涩嘶哑。然后,是身后压抑的、火山喷发前般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他还没来得及回头,一双铁钳般的手已经凶狠地从后方掐住了他的脖子,狠狠将他掼倒在地。后脑勺撞上坚硬冰冷的石材,剧痛瞬间炸开,随后是彻底淹没他的黑暗,以及颈骨在恐怖力道下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呻吟。肺部的空气被无情榨干,眼前炸开猩红的光点。
“离开我?你休想!永远也别想!”那声音扭曲狂暴,如同来自地狱的咆哮,每一个字都带着滚烫的、足以熔断神经的怨恨,直接烫在他的耳膜上。
混乱,挣扎,绝望如黑色淤泥淹没头顶。紧接着,是一阵仿佛自灵魂最深处爆裂开的绞痛,撕心裂肺。汹涌而出的温热液体瞬间浸透了雪白的棉质长裙,在地面上蔓延开触目惊心的浓稠红痕……
法兰西猛地睁开眼,急促地喘着气,像一条搁浅的鱼。台灯微弱的光此刻显得如此刺目。他低下头,腹部圆润温暖的轮廓清晰地印在薄薄的羊毛衫下。现实和记忆的血腥碎片重叠又分离。是诺曼。不是亚瑟。掌心下,孩子再一次轻轻顶了他一下,带着不容置疑的生命力。
就在这时,书房沉重的橡木门无声地滑开一道缝隙,一股带着壁炉暖意和某种冷冽须后水气味的空气涌了进来,瞬间冲淡了室内单一的寒气。
法兰西的身体瞬间绷紧,如同一张拉满的弓。搁在腹上的手指微微陷了下去,不自觉地做出保护的姿态,然后才僵硬地松开。他没有抬眼,只是侧脸的线条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愈发冷硬。
英吉利的身影出现在门口,高大挺拔,剪裁考究的深色晨礼服包裹着他。他脸上带着一种近乎刻意的、竭力柔化的神情,仿佛小心翼翼地捧着某种易碎的瓷器,脚步轻缓地走近,踩在厚实的波斯地毯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夜里冷,我给你拿了过来。”
他的声音低沉悦耳,几乎可以称得上温柔,与法庭里那个野兽般的嗓音判若两人。一只骨节分明的手递了过来,指尖捏着一条东西,在灯下折射出柔和的光晕。是一条珍珠项链。饱满圆润的南洋珠,颗颗莹白,透着温润内敛的光泽。
法兰西的目光终于从桌面的文件上抬起,落在那串珍珠上。光芒安静流淌。有一瞬,他似乎从那些珍珠内部极深处,看到了某种与精致外表截然不同的、坚硬的沙砾核心。粗糙磨人。像极了这段关系的内里。他面无表情地看了片刻,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头,几乎难以察觉。
英吉利的脸上掠过一丝细微但清晰的放松,如同冰面裂开一丝缝隙。他向前一步,将那沉甸甸的珠串轻轻放在法兰西摊开的、等待在灯光下的掌心里。珍珠触碰指尖的一刹那,两人都没有再动,维持着这个奇异的交接姿态,仿佛在进行某种静默的仪式。
然后,英吉利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更低,带着一种笨拙而刻意的讨好:“很美,很衬你。”
法兰西修长苍白的手指缓缓握拢,将那些冰凉的珠子攥入掌心。指腹摩挲着珍珠温润的表层,像要探知它深处坚硬的内核。他没有回应那句赞美,只是将目光重新投向摊开的文件,纸张边缘锋利得如同刀刃。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高大的阴影就凝固在他身后咫尺之遥,像一片永不退去的寒冬,一种无形的、沉甸甸的压力弥散开来,笼罩着书桌这一隅昏黄的光晕。
那目光如有实质,炙热又冰冷,交织着强烈的占有和某种难以名状的渴求,粘稠地、固执地停留在他的后颈。这无声的注视比任何言语更具压迫。他颈后那块微凹的、异常敏感的皮肤开始僵硬发烫,仿佛又感受到了当年法庭地板上,那要将他彻底碾碎掐断的狂暴指压。
就在法兰西几乎要承受不住这沉重凝滞的注视时,英吉利带着那份几乎从不离开的、令人不安的克制开口了。他的声音竭力放得平稳,却掩不住一丝细线般的紧绷和急迫:“巴黎银行在印度支那的橡胶份额……”
法兰西的目光停在文件上某个无关紧要的数字上,指腹却无意识地、一下下用力捻搓着掌心里那颗圆润的珍珠,坚硬的珠核硌着皮肤,带来细微而确切的痛感。他并未抬眼,也没有一丝表情变化,只将那份推到他手边的、早已仔细阅览签署好名字的合同文件,往前挪了半寸。
纸张在厚重的红木桌面上摩擦,发出沙沙的轻响。
这轻微的挪动仿佛包含了所有答案。房间里只剩下台灯里火焰跃动般的微弱嘶声,以及两人之间那条凝固冰冷的空气带。法兰西维持着绝对的静默,侧脸在灯光下如冰冷的瓷器。颈后那道无形的目光重量,随着这凝滞的沉默,一点点加重,如同水银倾灌。
终于,英吉利猛地吸了一口气,那声音在寂静中异常清晰,像是强行压下了胸腔里翻腾的猛兽。他伸出手,不是去拿文件,那只骨节分明、在光线下甚至显得文雅的手,带着压抑的力道,猛地撑在了深色泛着冷光的桌面上。
“你就这么……不想和我说话?”他的声音陡然压低了,像闷雷滚过阴郁的天空,每一个字都裹着即将碎裂的薄冰。
法兰西的身体在宽大的扶手椅里彻底僵死,只有握着珍珠项链的指尖用力到骨节发白。他没有动,视线甚至未曾从文件上抬起丝毫,但那股萦绕颈后的、混合着暴戾与绝望的气息,瞬间将他拉回到那个血色的午夜。
冰冷坚硬的地板。粗暴的撕扯。燃烧的疼痛与深入骨髓的羞辱感。绝望像一块沉重的湿布死死捂住了口鼻。窗外是没有星星的浓重黑暗……
紧接着,记忆的画面被另一片无边无际的血色淹没,来自他的身体内部……是亚瑟,那个被他短暂拥有,又永远失去的小生命……
桌面冰冷坚硬的触感透过袖口传来。他背脊挺得笔直,像一尊拒绝融化的冰雕。
撑在桌面上的那只手,手背的青筋因克制而狰狞地隆起、跳动,像底下囚禁着濒临爆发的岩浆。桌面上摊开的文件被撑开的手掌边缘挤压出愤怒的褶皱。
法兰西的沉默,如同淬炼出的最坚硬的盾牌。良久,英吉利那仿佛在岩浆里滚过的灼热呼吸,缓缓从法兰西的颈后撤离,带起一阵细微的、令人不适的凉风。那撑在桌面上、指节绷紧到泛白的手,终于猛地抽离。
沉重而疲惫的脚步声响起,走向门口,碾过厚厚的地毯,无声地控诉着那令人窒息的失望和压抑未散的雷霆怒火。门轴轻轻转动,像一声无奈的叹息,最终悄然合拢,将所有的风暴暂时阻隔在门外。
那冰冷的珠链依旧被法兰西紧紧攥在手心,硌出的印记深深印在皮肤上,像是某种无法愈合的烙印。书房里重归死寂,只剩下他沉而紊乱的呼吸在空旷中突兀地回响。他缓缓松开僵硬的手指,让那串沉重冰冷的东西滑落进丝绒盒里。手指无意识地落在再次微微凸起的腹部上,带着一种近乎贪婪的、汲取暖意般的依恋,缓缓摩挲着。
这一次,必须不一样。
英吉利庄园深处的育婴室,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温暖的壁炉驱散了英格兰特有的阴冷湿气,壁炉前的纯白羊绒地毯厚实而柔软,仿佛一片精心构筑的雪野。壁炉上方,古老的钟摆发出单调的咔哒声,是这寂静空间里唯一的脉搏。
法兰西屈膝跪坐在这片“雪野”中央,身上一件宽松柔软的米白色细羊绒衫,衬得他脸色苍白依旧,唯独眉眼间凝着一层近乎透明的柔和光晕。他微微垂首,目光专注如凝固的湖水,落在依偎在怀中的襁褓上。
几个月大的诺曼,有着柔软得不可思议的淡金色胎毛和长长的、让人心头发颤的睫毛。他正咿咿呀呀地嘟哝着什么,粉嫩的小拳头在空气中轻轻挥舞,像在指挥一场只有他能听见的音乐会。那双清澈如天空碎片的眼睛,偶尔会茫然地掠过壁炉架上投下的暖光阴影,最终却总是执着地落回近在咫尺的法兰西脸上。
法兰西的指腹小心翼翼地拂过那娇嫩的、带着奶香的脸颊,指尖感受着生命细微的温热与活力。每一次触碰,都像有一道微弱的暖流从他冰冷的指尖注入枯寂的心底。诺曼咯咯的笑声,比风铃更清澈欢快,带着不设防的天真,撞击在育婴室温厚的墙壁上,碎裂成一片短暂却真实的光亮。
然而这片纯粹的光亮中,始终矗立着一道巨大无形的阴影。
法兰西的余光始终锁定在房间另一端巨大的桃心木扶手椅里。英吉利坐在那里,身姿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挺拔,但整个人却如同冻结在深水之下。昂贵的银灰色马甲下,胸膛起伏的节奏被极力压抑着。手中那张摊开的《泰晤士报》很久没有被翻动过一次,目光穿透脆弱的纸张,牢牢钉在壁炉前那片温馨的图景上。
他眼神里有某种巨大的、未曾被满足的空洞。凝视着那具依偎在法兰西怀中的小小身躯时,眼神滚烫得近乎灼人,却奇异地被一层厚厚的、冰冷的东西包裹,沉重而复杂。那眼神混合着一种原始的、几乎要满溢出来的渴望,以及被强大意志死死封住的巨大力量,其间还夹杂着难言的沮丧和被放逐般的孤寂。他像一座渴望喷发却又被强行冷却的火山,僵持在那座名贵的椅子里,只有指节用力到泛白泄露了冰山底下的熔岩。
钟摆的机械节奏冰冷地切割着室内的寂静。壁炉里木炭无声地燃烧,橙红火光在法兰西苍白的面孔和诺曼娇嫩的睡颜上跳跃。英吉利如同一个被施了定身咒的雕塑,只有报纸边缘在他无意识的收紧力下,发出细微而压抑的沙沙声,如同一种无声的哀求或低泣。
地毯上的温暖图景与扶手椅里散发出的冰寒孤寂,无声地对峙着,如同隔着一道无形的悬崖。
壁炉的火光在诺曼清澈如天空碎片的眼眸里投下跳跃的光点。他吃饱了奶,心满意足地躺在法兰西臂弯里,睁着那双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随意地捕捉着房间里流动的光与影。他无意识的目光终于掠过那片温软的毯子、燃烧的火焰,最后漫无目的地停驻在那张巨大的、深色桃心木椅子的方向。
英吉利的存在,如同一片沉重复杂的磁场,无法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