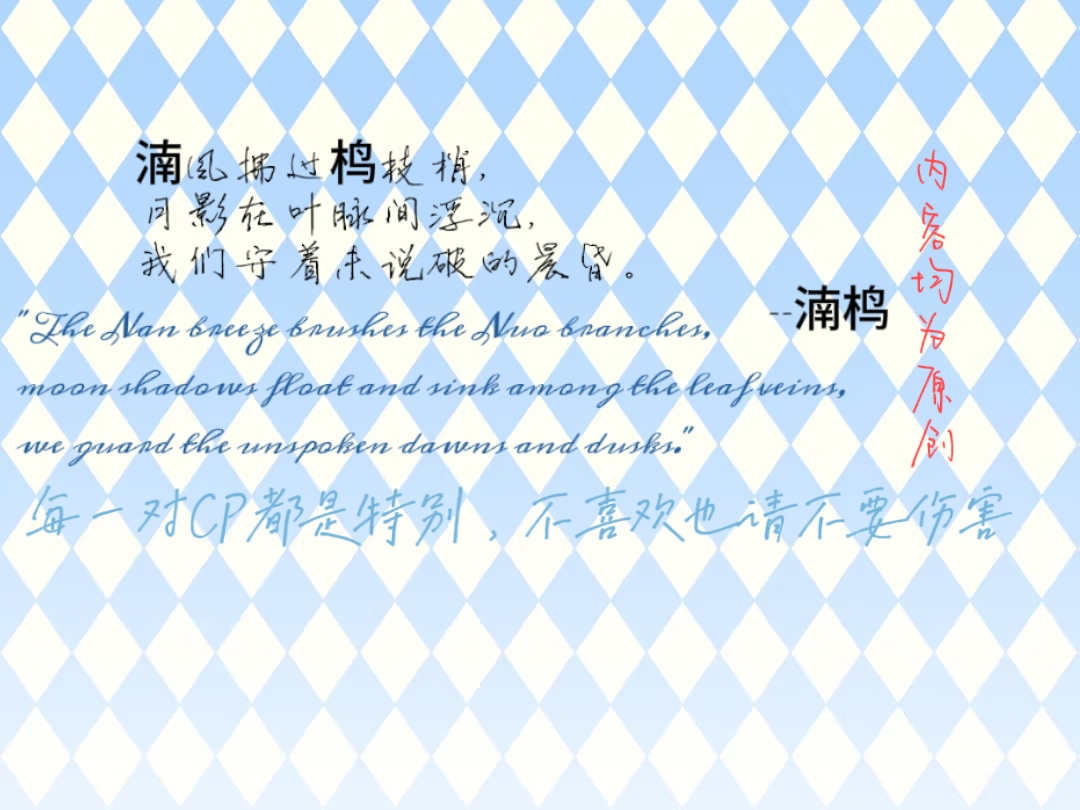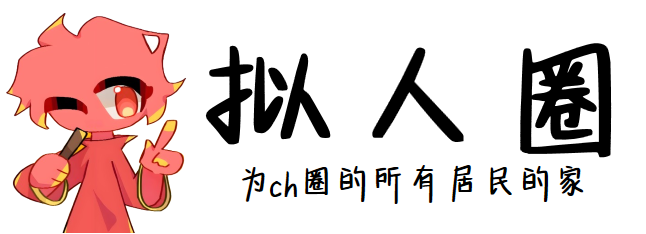(1)
1949年的莫斯科,冬雪初融。瓷站在克里姆林宫恢弘的红色围墙外,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结成霜。他拢了拢略显单薄的深蓝色中山装,这是他为这次重要会议特意准备的——作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代表,第一次踏上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土地。
“同志,你看起来需要帮助。”一个带着斯拉夫腔调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瓷转身,看到一位身材高挑的青年正对他微笑。那人有着浅棕色微卷的短发,灰蓝色的眼睛像是贝尔格莱德多瑙河上泛起的晨光。他穿着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装,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红星徽章。
“我在找第三会议厅。”瓷用尚不熟练的俄语回答。
“真巧,我也是去那里。”青年伸出手,“我是南,南斯拉夫代表团的。”
“瓷,来自中国。”他握住那只手,感受到对方掌心传来的温度,比莫斯科的冬日温暖得多。
两人并肩走在克里姆林宫的长廊里,大理石地面映出他们的倒影。南比瓷高出约半个头,步伐却自然地配合着他的节奏。
“你们刚刚完成了一场壮丽的革命,”南的声音里带着真诚的钦佩,“我们也在走相似的路。”
瓷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革命只是开始,建设才是更艰难的征程。”
会议厅门前,苏正被一群东欧国家代表簇拥着。看到瓷和南一起走来,他那双钢灰色的眼睛微微眯起。
“啊!我们的小同志和南斯拉夫同志一起来了!”苏的声音如同西伯利亚的寒风,表面热情却暗藏锋芒。他高大的身躯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堡垒,军装外套上的勋章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我们在门口偶遇。”南简短地回答,嘴角的笑意淡了几分。
会议冗长而沉闷,各国代表轮番发言,大多是对苏的赞美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歌颂。瓷注意到南在听到某些言论时,修长的手指会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敲;而苏的目光则时不时扫过他们两人,眼神难以捉摸。
会后晚宴上,瓷独自站在角落,观察着这场政治舞蹈。他的俄语还不够流利,难以融入那些快速的交谈。
“不喜欢这种场合?”南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旁,手里拿着两杯伏特加。
瓷接过酒杯,苦笑道:“我更习惯安静地做事。”
“我也是。”南的酒杯轻轻碰了碰他的,“这些宴会总是让我想起战前的贝尔格莱德沙龙——表面光鲜,暗流涌动。”
他们找到一处僻静的阳台,远离喧嚣。莫斯科的夜空繁星点点,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交织。
“你们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法西斯,”瓷说,“这很了不起。”
南的眼睛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明亮:“是的,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解放了祖国。这也是为什么……”他停顿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对某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
瓷会意地点头。他已经听说了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也是。”瓷轻声说,“我们感谢苏的帮助,但每个国家的路终究要自己走。”
两人的目光在夜色中交汇,一种无声的理解在流动。就在这时,阳台的门被猛地推开,苏高大的身影填满了整个门框。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他的声音如同雷霆,脸上的笑容不达眼底,“大家都在找你们呢!”